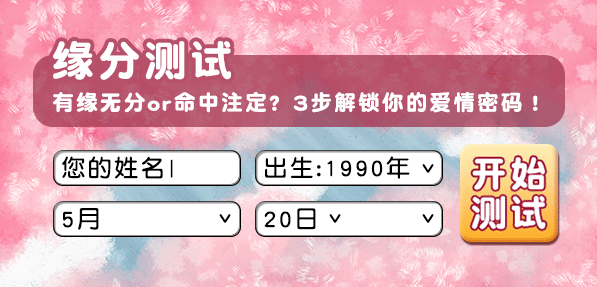694是什么意思(694是什么意思爱情)

细辨条形码
条形码通常应用于商品包装上,在超市和商店里可以说随处可见。条形码目前是商品能够流通于国际市场的一种通用的国际语言,是商品身份证的国际统一编号。在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条形码广泛用作商品标志,已成国际化的规则和惯例。
条形码是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空及其相应字符组成的标记,用以表示一定的产品信息,专供机器识读的一种特殊符号。条形码种类有许多,常见的大概有二十多种,而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的当属EAN-13(国际商品条码),它是由30条黑线组成,代表了一个长度为13位的阿拉伯数字,对应某个国家或地区某个制造厂商生产的某个产品。
图源:baidu
条形码的设想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约翰·科芒德的古怪的发明家,突发奇想欲对邮政单据实现自动分检,这在当时绝对是令人惊奇的创意。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信封上做条码标记,条码中的信息是收信人的地址,有点类似如今的邮政编码。设计方案也比较简单直接,即一个“条”表示数字“1”,二个“条”表示数字“2”,以此类推,就诞生了最早的条码标识。后来,他又发明了由扫描器和译码器组成的条码识读设备。
到了40年代,美国乔·伍德兰德(Joe Wood Land)和伯尼·西尔沃(Berny Silver)在与食品连锁店老板交流开发自动化结帐系统的想法后,开始着手研究用条形码表示食品项目及自动识别的设备,并于1949年获得了美国专利。该专利的图案很像微型射箭靶,被称为“公牛眼”代码,在原理上,“公牛眼”代码与后来的条形码很相近,所以被认为是条形码的雏型。遗憾的是当时的工艺和商品经济还没有能力印制出这种码,但这并不影响乔•伍德兰德成为北美统一代码UPC码奠基人的地位。因为在其后的20年中,许多发明家受“公牛眼”代码的启发取得各项相关专利,使条形码的拓展研究和应用取得长足的进步。
1970年,美国超级市场委员会制定出通用商品代码UPC码,许多团体也提出了各种条形码符号方案,UPC码首先在杂货零售业中试用,这为以后条形码的统一和广泛采用奠定了基础。
1973年,美国统一编码协会(UCC)建立了UPC条形码系统,实现了该码制标准化。同年,食品杂货业把UPC码作为该行业的通用标准码制,为条形码技术在商业流通销售领域里的广泛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6年,UPC码在美国和加拿大超级市场上得到成功应用,欧洲人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次年,欧洲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欧洲物品编码EAN-13和EAN-8码,在欧洲各成员国间通用,并正式成立了欧洲物品编码协会(简称EAN)。到了1981年由于EAN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故改名为“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简称IAN。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习惯,一直被称为EAN。
EAN条形码从根本上解决了品种繁多的商品编码的需求。以目前最为常见的EAN-13条形码为例(图1),它的构成是,由代表12位数字的产品代码和1位校验码组成。产品代码的前3位为国家代码;中间4位数字为厂商代码;后5位数字为产品代码,最后一位数字是校验码。
在代表不同生产企业的四位数中,每个数位都有10种选择,可以供10×10×10×10=10000(个)不同的企业使用;在表示不同商品的五位数中,每个数位也可选择0-9中的任意一个,一个企业可以有10×10×10×10×10=100000(个)不同种类的产品使用条形码。因为“690、691、692、693、694”为我国商品的前缀码,则可以提供5×10000 =50000(个)不同的企业使用50000×100000= 5000 000 000(个)不同的条形码。通俗地解释,就是采用690- 694为前缀代表中国商品的条形码可达50亿个。
那么,条形码中的校验码又是怎么确定的呢?其实它是根据前12位数确定的。在条形码的13位数中,将偶数位上数的和乘3后,与奇数位上数的和相加,要求最后的和为10的倍数,从而来确定第13位的校验码。
不妨以图1的条形码690123456789X为例,判断最后的校验码2是如何得到的呢?
根据“偶数位上数字之和×3+奇数位上数字之和+校验码X=10的倍数”,则有(6+0+2+4+6+8+X)+ (9+1+3+5+7+9)×3=10的倍数,即128+X=10的倍数。因为X是一位数,所以满足条件的只有X=2,即最后一个校验码必须为2。如果不是,那么就说明这个条形码是假码。
由于EAN条形码具有高度的查核能力,扫描操作快速简捷、方便可靠,迄今为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成为该协会成员国,我国于1991年7月加入该协会,条形码全球统一化的趋势日趋明朗。国际物品编码协会也将组织名称由EAN正式变更为GS1,建立并推行“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和通用商务标准——EAN·UCC系统”,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通用商务语言。
总体而言,条形码及技术起源于20年代,开发于40年代、研究于60年代、应用于70年代、普及于8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生活国际化、文化国土化的资讯社会时代,引发世界流通领域里的重大变革。
征稿启事 中国科学探索中心微信公众号欢迎赐稿!稿件内容以反伪破迷为核心思想,科学普及、科学文化、科技哲学、科学与公众、世俗人文主义、科技伦理等领域均可涉及,旨在将科学探索结果无偏见地告知公众,避免公众上当受骗。稿件一经采用,将奉上稿酬。 投稿邮箱:kpsbsh2017@163中国科学探索中心 崇尚科学 反伪破迷分享收藏点赞在看694斤世界最胖女子收获年轻男友真正的爱情
世界最胖女子夏里蒂·皮尔斯重达765磅(约合694斤),体重已经超负荷了。
夏里蒂的男友汤尼今年24岁小年轻,6年前他们通过夏里蒂的女儿相知相爱,汤尼希望帮她找到一名医生进行手术以挽救生命,然后结婚。
二人经常秀恩爱,把亲热的照片发到社交网站上。
为了能够实现在婚礼上与男友“彻夜跳舞”的愿望,她发誓要减到医院愿意给她做减肥手术的体重。
夏里蒂·皮尔斯发胖之前照片。
看到这报道后,你是否又开始相信爱情呢?
破局食用油进口依赖 提高油脂油料自给率
中国是油料进口大国,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让“油瓶子”里尽可能多装中国油。为推动脂质科学与健康相关领域的研究和产业的创新发展,在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国际脂质科学与健康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脂质科学与健康等前沿学术话题进行了专题报告和讨论,包括开发昆虫油脂、改良油脂提取工艺等,以提高油脂自给率,破解食用油依赖进口的难题。
供求缺口大,净进口量逐年攀升
我国是全球油料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国内油料作物种植规模仅次于粮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油料生产快速发展,2020年全国油料作物(含油菜、大豆、花生、向日葵、芝麻、胡麻)种植面积达到3.5亿亩(占世界约7%),比2019年增长1.6%;油料作物总产量约5700万吨(占世界约20%),比2019年增长约2.6%,油菜、花生、大豆占中国油料作物总产量的94.2%。
2019年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2384万吨,占世界食用油产量10.5%,排名世界第2;从食用消费植物油脂构成来看,主要食用油品种包括大豆油、菜籽油、棕榈油、花生油等。
从生产规模看,全国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在规模上仅次于水稻、玉米、小麦三大谷类粮食作物。从品种看,全国油菜、大豆和花生三者种植面积与总产量之和均占油料作物90%以上,是油料生产和利用的主体。从品质看,各种油料均培育出高含油量品种,大豆和花生培育出高蛋白品种,油菜和花生培育出高油酸品种。从产区分布看,长江流域的冬油菜、东北地区的大豆、黄淮地区的花生、北方干旱盐碱地区的向日葵,是油料作物种植的集中产区和优势产区。
“尽管我国油料生产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随着消费需求加快增长,国产植物油面临自给率偏低、进口依赖度过高的现实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黄风洪表示,2021年全国植物油脂消费总量为4254.5万吨,食用油消费同步增加达3708万吨(占全球消费的17.7%),是2000年的3倍。2010年以来我国食用油消费增长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人均油料油脂消费同步增长,2021年我国人均食用油的消费量为30.1千克,超过了2021年世界人均食用油消费量27千克的水平。
由于产需缺口较大,我国油料和食用植物油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以棕榈油为例,需求端在国内,供给端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油脂油料价格波动频繁,产业稳定健康发展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
黄风洪介绍,1999年之后我国取消了大豆的配额限制,降低关税,国内外大豆价差明显,我国油料产品进口量激增。1998年我国油籽进口量为461万吨,1999年增至694万吨,是上年的1.5倍,到2020年达到1.08亿吨,是2000年的15倍。大豆进口量是国产的5.1倍,芝麻是2.3倍;油菜籽进口量逐年增加,2020年达到311万吨;2020年花生进口量超过国产。
2021年食用油自给率持续下降,2021年国内压榨油共计3708万吨,其中,国产油料压榨1150万吨(油菜、花生)占31%、进口油料压榨1700万吨(大豆、油菜)占46%、进口植物油858万吨(棕油、菜籽油等)占23%,进口依赖度高达70%。
因而,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提高国产食用植物油自给率的任务愈加紧迫。
用科学的方法提高自给率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让“油瓶子”里尽可能多装中国油。农业农村部提出把扩大大豆油料生产作为明年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
要树立大食物观,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油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黄风洪表示:“要实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见到可考核的成效,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含油量。”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蔡光勤表示,与粮食作物不同,油脂是油料作物的主要产品,产油量是衡量油料作物最重要的指标,推广品种的含油量在42%—45%左右,与加拿大等主要油菜生产国相比低4%—6%。
“含油量的遗传机制不明是制约我国油菜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之一。”蔡光勤介绍,油料植物种子发育过程中物质积累(油脂和蛋白质等)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其中,油脂净积累存在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如何破解油脂降解严重影响油料植物种子油脂的净积累是关键的科学问题。
油脂降解是植物维持生命活动重要的生物学现象,如为种子萌发提供能量、应对非生物胁迫、影响种子发育过程中油脂积累等。“但目前对油脂分解代谢的代谢调控还不清楚,因此挖掘和识别油脂降解调控的关键基因,对于油菜籽等油料作物含油量的遗传改良具有重要意义。”蔡光勤表示。
发育的种子中,油脂合成与降解同时发生,很难找到油脂降解的关键基因。萌发的种子中,主要以油脂降解为主,为后期幼苗的建成提供最主要的能量,更容易开展油脂降解机制的研究。
通过对种子发芽率和无糖培养基成苗的筛选,鉴定到油脂降解调控关键转录因子AHL4。AHL4通过抑制参与三酰甘油水解和脂肪酸氧化的特定基因的表达来抑制脂质分解代谢。AHL4过表达株系种子含油量较野生型增加4.5%—6.7%,AHL4过表达株系种子中亚油酸含量显著高于野生型。蔡光勤表示,本研究为油菜乃至其他油料作物的油料产量遗传改良提供了“要提高油料作物含油量,可抑制种子发育过程中油脂的降解”这一新策略。
昆虫蛋白,作为可替代蛋白质来源之一,已经被大众所熟知并运用到饮料、休闲零食、蛋白棒等多个食品领域分支里。昆虫脂肪同样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昆虫油脂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消化性能好,微量元素丰富,糖分含量低,昆虫脂质及油脂除可作为优质营养调和食用油外,还可用于制药工业及其他行业,如黄粉虫可作保健品添加用油、化妆品添加剂和变压器用油,蚕蛹油可用于制备降低胆固醇的药物、润滑油等,可食用昆虫的价值被更多地挖掘出来。
目前世界上已经知道的昆虫种类已超过100万种,其中已确定3650余种昆虫可供食用,我国食用昆虫种类据推测有800多种。昆虫体内脂质的含量,随昆虫的生活史而变动,但总的来说,昆虫的脂肪含量丰富,许多昆虫的脂肪比例达30%甚至40%以上。此外,昆虫体内也包含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等。“昆虫脂质是昆虫体内的重要成分,开发昆虫脂质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科技大学教授王俊介绍。
蚕蛹中含有丰富的n-3不饱和脂肪酸,如α-亚麻酸,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昆虫体内存在的脂类、蛋白质等成分具有独特的性质,用压制法提取油脂虽工艺操作简单、生产规模大小灵活,但出油效率低。目前大部分采用的浸出法,劳动力强度低、生产效率高,但有机溶剂使用量大、安全性较差、对环境不友好。水酶法是以水代法为基础,在特定条件下利用生物酶破坏细胞结构,促使油脂释放的一种油脂提取方法,具有提取条件温和、绿色安全、可同时分离出油脂和蛋白质等产品的优点。
王俊团队采用磁性纳米颗粒固定化酶等方法改进了水酶法,以达到更绿色、安全、高效且经济地提取昆虫油脂。结果显示,催化性能显著提升,提取时间比改进前的水酶法减少了2小时,仅需4小时,过程所需温度从原本的80摄氏度下降到50摄氏度,且不需要反复多次提取,使用的溶剂为水,通过离心后溶剂可重复利用。改进前的水酶法提取率为70%,改进后的水酶法提取率为93.13%,提油效果显著提升。
(王佳仪 刘艳芳)
重磅!关于新冠病毒起源,22位科学家联名撰写观点文章(全文)
7月16日,由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撰写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观点文章\"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在线发表于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文章运用“盲眼钟表匠”理论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人为制造。
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英] 理查德·道金斯《盲眼钟表匠》
文章作者:
吴仲义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文海军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陆剑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系生物信息学中心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苏晓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系生物信息学中心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爱丽丝·休斯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景观生态小组]
翟巍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化与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陈晨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世纪坛医院生物医学创新中心]
陈华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李明锟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宋述慧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钱朝晖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王奇慧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陈冰洁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郭子骁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阮永森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吕雪梅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魏辅文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金力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康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薛勇彪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赵国屏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张亚平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全文翻译如下:
与2003年的SARS-CoV相比,SARS-CoV-2(新冠病毒)不仅在人群中具有极高的适应性,也势必已经具有了更广泛的从动物宿主向人类宿主的适应性转变。根据“盲眼钟表匠”的论点,该适应性转变仅可能在当前疫情开始之前,并在一步步自然选择的驱动下才会发生。基于这一理论,SARS-CoV-2不可能在大城市的动物市场里进化出来,更不可能产生于实验室。关于SARS-CoV-2起源的讨论需要考虑长期的适应性转变过程,相关的科学模型已经推演并论述了这一过程。
近期,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均有很多关于继续调查SARS-CoV-2的起源的呼声,例如,近期《科学》杂志就曾对此发出过一篇简报(Bloom et al., 2021)。本文旨在严格基于科学原则,对SARS-CoV-2的生物学起源做出评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非科学视角的观点。
基于所谓非预期的基因组特征,有一些学者提出SARS-CoV-2不可能在自然界中进化出来(Sallard et al., 2021; Segreto and Deigin, 2020)。然而SARS-CoV-2基因组进化到其目前的状态,实际上并不违背已知的自然规律,关于SARS-CoV-2非自然起源的说法毫无实际意义。除非能找到带有明显人工设计特征的毒株(如目前追踪细胞谱系时常用的条形码),否则当务之急和更有成效的做法,应该是专注于探究与SARS-CoV-2起源有关的自然过程。
首先,在开始调研之前,我们必须明确“起源”的含义。任何生物的起源,无论是人、狗或被子植物,往往都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生物特征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步步形成。因此,一个物种早期的进化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需要走过漫长的地质历史。如果我们把生物起源仅仅看作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一起事件,关于它的讨论自然就不会得到共识。那么,SARS-CoV-2的起源究竟有什么含义?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 这种病毒是花费了多少时间、散播过多远的地域、又如何进化到能够如此完美地在人群中传播的地步。SARS-CoV-2的起源应该是从它还只在某些野生动物中有良好的适应性开始,之后,它应该发生过从动物宿主生态位到到人类宿主生态位的适应性转变。
适应性转变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进化,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畅销书《盲眼钟表匠》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论述。1794年,威廉·佩利提出,完美的适应,就像一块精致的手表,它的出现意味着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是非自然的过程(Paley, 1829)。这种与进化论不符的错误认识,正是道金斯“盲眼钟表匠”论述所抨击的。“盲眼钟表匠”理论认为,进化是一步步逐渐进行的,每一步都会从一堆随机的“修修补补”突变中保留下一些对生物体来说微小、但可以提高适应度的改变,聚沙成塔。这些不起眼的改进最终积累起来,把生物体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Dawkins, 1996)。
适应性转变的过程应该是SARS-CoV-2起源的核心问题,但遗憾的是,它被有意忽视了。关于SARS-CoV-2的起源,目前有两类流行的观点。第一类是SARS-CoV-2经历了自然起源过程。这类观点认为,一些野生动物在与人类接触时已经携带了可以完全适应人类宿主的SARS-CoV-2。这种通过随机动力来实现完美“预适应”的观点,是威廉·佩利等这些相信存在“造物主”的人所反对的。这类观点的证据是,鉴于2019年12月以来病毒极快的传播速度,SARS-CoV-2似乎在疫情开始时就非常适应人类宿主。第二类观点认为,SARS-CoV-2从某些病毒学实验室(这类观点的拥护者会从他们的立场提出实验室的特征)泄露出来的。泄露出的病毒是经过诱变、遗传重组、基因组重排等种种传统病毒学实验的产物。病毒泄露后意外引发了新冠疫情。这种观点也认为病毒在传播初始就已经是完美的预适应产品。
但目前已有的证据都不支持这种认为病毒进化并没有经过自然选择的预适应观点:
首先,有许多研究采取了“合理设计”的方法,改变了病毒的进化方向,例如逃避免疫反应或改变它们的宿主范围(Bajic et al., 2019; Becker et al., 2008; Menachery et al., 2015)。然而正如一项著名的研究所述(Menachery et al., 2015),这种方法可以把病毒往预期的样子进行改变,但远远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疫情。
其次,以上研究的结果表明,病毒的适应性进化需要通过自然选择来实现。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Huynh et al., 2012; Normile, 2013)。
第三,小鼠本来不会感染SARS-CoV-2,但在实验室中,已经有研究人员用人工选择的方法成功选择出了能够感染小鼠的SARS-CoV-2毒株(Dinnon et al., 2020; Gu et al., 2020; Leist et al., 2020)。研究结果显示,使SARS-CoV-2变得能够感染小鼠的突变只占所有产生的突变的很小一部分,说明这些突变一定经历过自然选择严苛的筛选。事实上,在2003-2004年疫情和之后的COVID-19疫情中,能够广泛传播的新型毒株日益增多(Davies et al., 2021; Korber et al., 2020; Tegally et al., 2020; Voloch et al., 2020),这充分证明了自然选择的力量。
从非进化的视角,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异议:不能排除病毒完全预适应人类宿主的可能。这与戈尔德施米特“有希望的怪物”假说类似(Goldschmidt, 1982)。我们想要指出,即使按照这种已经不被学界所接受的观点,极低概率事件(即“有希望的怪物”)也只可能在漫长的进化时间跨度上以及很大的地理区域内发生。然而,一些人却无科学根据地提出,SARS-CoV-2预适应地进化出近乎完美的状态这种小概率事件,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发生。
根据我们的推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病毒在人群中已经经历了某些形式的逐步进化,不然SARS-CoV-2不会有如此强大的适应性。问题在于,如果病毒要在所有这些步骤完后才能产生最终的适应性,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盲眼钟表匠”理论指出,每一步的改良都会带来新的优势,即便这一优势有多么微不足道。为此,有研究提出了SARS-CoV-2的渐进式演化模型(Ruan et al., 2021)。在此模型中,病毒的PL0(原发地)应当人迹稀少,是动物宿主的栖息地,病毒得以在此处与其动物宿主展开“军备竞赛”。随后,病毒偶然扩散到了没有群体免疫的人群中间。第一个疫情暴发地(即PL1),准确来讲与PL0有所不同,原因是PL1里的人群对此种病毒没有免疫力,说明人群事先并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艾滋病(AIDS)的流行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Crosby, 2003; Sharp and Hahn, 2011)。
除上述概念性论证外,大量看似无关联的报道也同样指出,可能存在区别于PL1的PL0。近期的一篇报道特别指出,在美国2019年12月采集的样品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对应的IgG抗体(Althoff et al., 2021)。其他报道也显示出,在2019年早些时候,不同行政地区内出现过零散的COVID-19疑似病例(La Rosa et al., 2021; Randazzo et al., 2020)。虽然很难去证实这些历史记录,考虑到病毒早期侵入的高度随机性,病毒在从PL0成功入侵到PL1之前,应该已经历了多次失败(Ruan et al., 2020; Ruan et al., 2021)。我们已经知道蝙蝠中自然携带着多种冠状病毒,几乎涵盖了整个冠状病毒家族,给病毒溢出事件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Zhou et al., 2021)。
起源问题的研究需要理论先于实验,这一点与很多其他生物学研究不同。研究人员进行实证调查时,需要先知道所搜寻的目标是什么,就像警察需要知道抢劫银行的嫌疑犯的长相。即便理论模型是正确的,都有可能找不到目标;错误的理论(就COVID-19而言,则是空白模型)就更会将追踪引入歧途。从Ruan等发表的理论推演中可以看出(Ruan et al., 2020; Ruan et al., 2021),人和动物频繁出入流动的大型城市中的海鲜市场,不可能提供PL0需要的、逐步实现病毒演化的稳定环境。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情况,但每个要求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人,应该像Ruan等的研究一样,明确“起源”的确切所指。
由于过去的20年里,已经发生了3次冠状病毒大流行,所以研究SARS-CoV-2的起源很重要。假如下个10年里再出现一次这样的疫情,那么对冠状病毒起源以及其起源后传播情况(Ruan et al., 2020; Ruan et al., 2021)进行科学解析,是人类做好准备、并防患于未然的最佳之路。
【References】
Althoff K.N., Schlueter D.J., Anton-Culver H., Cherry J., Denny J.C., Thomsen I., Karlson E.W., Havers F.P., Cicek M.S., Thibodeau S.N. (2021). Antibodies to SARS-CoV-2 in All of Us Research Program Participants, January 2-March 18, 2020.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Bajic G., Maron M.J., Adachi Y., Onodera T., McCarthy K.R., McGee C.E., Sempowski G.D., Takahashi Y., Kelsoe G., Kuraoka M., Schmidt A.G. (2019). Influenza Antigen Engineering Focuses Immune Responses to a Subdominant but Broadly Protective Viral Epitope. Cell Host & Microbe 25, 827-835.e826.
Becker M.M., Graham R.L., Donaldson E.F., Rockx B., Sims A.C., Sheahan T., Pickles R.J., Corti D., Johnston R.E., Baric R.S., Denison M.R. (2008). Synthetic recombinant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is infectious in cultured cells and in m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 19944.
Bloom J.D., Chan Y.A., Baric R.S., Bjorkman P.J., Cobey S., Deverman B.E., Fisman D.N., Gupta R., Iwasaki A., Lipsitch M., Medzhitov R., Neher R.A., Nielsen R., Patterson N., Stearns T., van Nimwegen E., Worobey M., Relman D.A. (2021). Investigate the origins of COVID-19. Science 372, 694.
Crosby A.W. (2003).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N.G., Abbott S., Barnard R.C., Jarvis C.I., Kucharski A.J., Munday J.D., Pearson C.A., Russell T.W., Tully D.C., Washburne A.D. (2021). Estimated transmissibility and impact of SARS-CoV-2 lineage B. 1.1. 7 in England. Science 372.
Dawkins R. (1996). The blind watchmaker: Why the evidence of evolution reveals a universe without design (WW Norton & Company).
Dinnon K.H., Leist S.R., Schäfer A., Edwards C.E., Martinez D.R., Montgomery S.A., West A., Yount B.L., Hou Y.J., Adams L.E. (2020). A mouse-adapted model of SARS-CoV-2 to test COVID-19 countermeasures. Nature 586, 560-566.
Goldschmidt R. (1982). The material basis of evolution, Vol 28 (Yale University Press).
Gu H., Chen Q., Yang G., He L., Fan H., Deng Y.-Q., Wang Y., Teng Y., Zhao Z., Cui Y., Li Y., Li X.-F., Li J., Zhang N.-N., Yang X., Chen S., Guo Y., Zhao G., Wang X., Luo D.-Y., Wang H., Yang X., Li Y., Han G., He Y., Zhou X., Geng S., Sheng X., Jiang S., Sun S., Qin C.-F., Zhou Y. (2020). Adaptation of SARS-CoV-2 in BALB/c mice for testing vaccine efficacy. Science 369, 1603.
Huynh J., Li S., Yount B., Smith A., Sturges L., Olsen J.C., Nagel J., Johnson J.B., Agnihothram S., Gates J.E. (2012). Evidence supporting a zoonotic origin of human coronavirus strain NL63. Journal of virology 86, 12816.
Korber B., Fischer W.M., Gnanakaran S., Yoon H., Theiler J., Abfalterer W., Hengartner N., Giorgi E.E., Bhattacharya T., Foley B. (2020). Tracking changes in SARS-CoV-2 Spike: evidence that D614G increases infectivity of the COVID-19 virus. Cell 182, 812-827. e819.
La Rosa G., Mancini P., Ferraro G.B., Veneri C., Iaconelli M., Bonadonna L., Lucentini L., Suffredini E. (2021). SARS-CoV-2 has been circulating in northern Italy since December 2019: Evidence fro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50, 141711.
Leist S.R., Dinnon K.H., Schäfer A., Tse L.V., Okuda K., Hou Y.J., West A., Edwards C.E., Sanders W., Fritch E.J., Gully K.L., Scobey T., Brown A.J., Sheahan T.P., Moorman N.J., Boucher R.C., Gralinski L.E., Montgomery S.A., Baric R.S. (2020). A Mouse-Adapted SARS-CoV-2 Induces Acute Lung Injury and Mortality in Standard Laboratory Mice. Cell 183, 1070-1085.e1012.
Menachery V.D., Yount B.L., Jr., Debbink K., Agnihothram S., Gralinski L.E., Plante J.A., Graham R.L., Scobey T., Ge X.Y., Donaldson E.F., Randell S.H., Lanzavecchia A., Marasco W.A., Shi Z.L., Baric R.S. (2015).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Nat Med 21, 1508-1513.
Normile D. (2013). Understanding the Enemy. Science 339, 1269.
Paley W. (1829). Natural Theology: or, 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Collected from the Appearances of Nature (Lincoln and Edmands).
Randazzo W., Truchado P., Cuevas-Ferrando E., Simón P., Allende A., Sánchez G. (2020). SARS-CoV-2 RNA in wastewater anticipated COVID-19 occurrence in a low prevalence area. Water Research 181, 115942.
Ruan Y., Luo Z., Tang X., Li G., Wen H., He X., Lu X., Lu J., Wu C.-I. (2020). On the founder effect in COVID-19 outbreaks – How many infected travelers may have started them all?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Ruan Y., Wen H., He X., Wu C.I. (2021).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and early evolution of a pandemic. Sci Bull (Beijing) 66, 1022-1029.
Sallard E., Halloy J., Casane D., Decroly E., van Helden J. (2021). Tracing the origins of SARS-COV-2 in coronavirus phylogenies: a review.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 1-17.
Segreto R., Deigin Y. (2020).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SARS‐CoV‐2 does not rule out a laboratory origin: SARS‐COV‐2 chimeric structure and furin cleavage site might be the result of genetic manipulation. BioEssays, 2000240.
Sharp P.M., Hahn B.H. (2011). Origins of HIV and the AIDS pandemic.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medicine 1, a006841.
Tegally H., Wilkinson E., Giovanetti M., Iranzadeh A., Fonseca V., Giandhari J., Doolabh D., Pillay S., San E.J., Msomi N. (2020). Emergence and rapid spread of a new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related coronavirus 2 (SARS-CoV-2) lineage with multiple spike mutations in South Africa. medRxiv.
Voloch C.M., Silva F R.d., de Almeida L.G.P., Cardoso C.C., Brustolini O.J., Gerber A.L., Guimarães A.P.d.C., Mariani D., Costa R.M.d., Ferreira O.C., Cavalcanti A.C., Frauches T.S., de Mello C.M.B., Galliez R.M., Faffe D.S., Castiñeiras T.M.P.P., Tanuri A., de Vasconcelos A.T.R. (2020).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SARS-CoV-2 lineage from Rio de Janeiro, Brazil. medRxiv, 2020.2012.2023.20248598.
Zhou H., Ji J., Chen X., Bi Y., Li J., Wang Q., Hu T., Song H., Zhao R., Chen Y. (2021).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bat coronaviruses sheds light 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SARS-CoV-2 and related viruses. Cell.
来源:中国科学杂志社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6-12八字型什么车(长得像八字的车标)
- 06-13八字木盛火焰(八字木火旺有哪些特征)
- 06-19八字查财禄(八字财禄是什么意思)
- 06-12八字壬水禄神(八字禄神是什么意思)
- 06-17八字天干癸壬(天干壬癸代表什么)
- 06-18八字大运吠呤(八字中的吠吟代表什么)
- 06-13八字天干辛壬(八字天干壬的五行属什么)
- 06-26观音灵签45签解签(观音灵签45签白话解签)
- 06-17八字无印心(八字中无印星说明什么)
- 06-22八字无水藏干(八字五行缺水是什么意思)
白羊座最新文章



- 01-31694是什么意思(694是什么意思爱情)
- 01-31十二门论(十二门论原文)
- 01-31三画的字有哪些(只有三画的字有哪些)
- 01-31诸葛亮活了多少岁(诸葛亮活了多少岁死)
- 01-31眼皮跳的预兆(眼皮跳的预兆是吉是凶时刻表)
- 01-31月柱孤辰(月柱孤辰是什么意思)
- 01-31男龙女兔(男龙女兔适合做夫妻吗)
- 01-318月18是什么星座(8月18号是什么星座)
- 01-31高官夫人
- 01-31风水探案师gl(相国嫡女与侯府家的傻子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