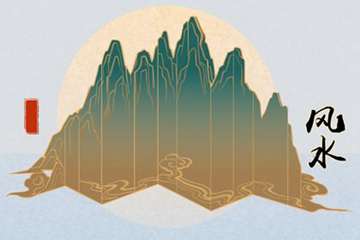一九八七(一九八七属什么生肖)

半世漂泊,不负“十亿个掌声”:但愿人长久,何日君再来?
中华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二九年的夏天,赵素桂在黑龙江哈尔滨出生。
赵素桂祖籍山东东平,东平县的地界上有个东平湖,古时候又叫梁山泊。
赵素桂女士的父亲赵守业时任国民政府哈尔滨市邮政局局长,母亲赋闲在家。她跟随父母亲在哈尔滨生活了五年,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人开进哈尔滨后,曾用数倍于其薪水的价钱拉拢赵守业,赵守业拒绝了。
赵家几口人辗转来到河南避难,赵素桂十五岁那年,在洛阳认识了邓枢。
△赵素桂与邓丽君
邓枢,字良岑,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氏,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校址甘肃),十四期生(一说十一期生),时年二十六岁。
邓枢自幼父母双亡,随后跟着姑妈生活,十四岁时参加国民革命军,从此不愁吃穿。
邓枢与赵素桂,经赵素桂祖母的朋友介绍认识。见面时,赵素桂躲躲闪闪不知如何是好。订婚那天,母亲张氏对她说:“这个人是你未来的丈夫。”
两年后的一九四三年,邓赵二人结婚。当时,赵素桂正在西安的宋美龄育英学校读书,婚礼在洛阳举行,夫妻二人婚后则生活在西安。
一年后,小两口儿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取名“小狗”。此时的邓枢已经回到部队参加抗日。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赵素桂就往脸上摸土灰,扮成乡下老太太。
有一次,为了躲避轰炸,赵素桂带着孩子挤进满满都是人的防空洞。人们担心孩子的哭声引来日本兵,把她娘俩赶了出去。
刚过不久,日本军机把那个防空洞炸成了废墟。
赵素桂和“小狗”暂时活了下来,一路从华北到了西南讨生活。“小狗”长到十个月大,还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夭折。
赵素桂苍老了很多。后来,她打听到邓枢部队,夫妻相见时,邓枢差点没认出眼前的结发妻子。
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邓长安、邓长顺先后出生,“长安”取自西安旧称,“长顺”寓意生活顺利。
一九四九年九月,邓枢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跟随兵败的军队坐上从广东汕头出发的船只,东渡到了台湾。
途中,赵素桂晕船严重,水喝下去,又吐出来。船在基隆停靠后,赵素桂卧病不起,后来一家人到了台北有名的“温泉之乡”北投,在那的眷属军营里生活了两个月。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专机机长衣复恩驾驶“中美号”,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载着离开了大陆。
后来,衣复恩曾说:“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
抵达台湾后,重新做了部署,邓枢被编为“后备军”驻守宜兰。
一九五一年,赵素桂在宜兰生下第三子,取名“长富”。
又过一年,邓枢升为中尉军衔。这时候,邓家人已经搬到了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居住。
田洋村,是台湾数百个“眷村”中的一个。
一九四六年,台湾人口约610万。
一九五〇年,这个数字激增至约745万。
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新住民。
在此背景下,用于安置军人及其家眷的“眷村”出现了,杨德昌、林青霞等艺人就都曾在眷村里生活过。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邓枢、赵素桂的第四个孩子出生,这次是个女孩。
邓枢为她取名“邓丽筠”。“丽筠”即为“美丽的青竹皮”。又过一年,丽筠有了胞弟邓长禧。
筠读“yún”,人们却慢慢叫成了“均”,多年后,邓丽筠取了个艺名,就叫邓丽君。
邓丽君还不满周岁的时候,邓枢由于工作调动,把家搬到了台东,后来又搬到屏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邓枢从部队退役,做起了摆面摊的生意。
生意不景气,赵素桂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卖面了。后来,邓家又开始卖馒头。
邓枢从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女儿“金鳞岂是池中物”。在他耳中,女儿的第一声啼哭都要比别的孩子嘹亮。
当时收音机流行放周璇的歌,邓丽君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哼唱。
赵素桂印象很深的是,女儿三岁那年,一个人跑去照相馆跟照相师傅说:“妈妈让我来照相。”可是赵素桂记得自己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幼稚园毕业典礼上,邓丽君作为代表发言,稿子读几遍就可以背下来。她个子小,够不着话筒,还要在脚底下垫上凳子。
邓丽君长到六岁,邓家又搬到了台北县芦洲。后来,邓丽君读芦洲国小了,邓枢的好友李成清经常来家里串门。李在军乐团里拉胡琴,他很喜欢邓丽君,教她唱歌。
八岁那年的一个雨天,邓丽君在院子里唱周璇的《缥缈歌》,正巧被路过的一位长者听到。
长者跑到邓丽君父母那里,非要收下这个小徒弟不可。
这位长者就是邓丽君的恩师常荫椿。
时间来到一九六三年,那时香港电懋与邵氏两家公司正打得火热。邵氏麾下的李翰祥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东南亚地区大受欢迎,力压电懋一筹。
黄梅调一时成风。邓丽君跟母亲去看了几次《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的曲子她就都会唱了。
常荫椿瞒着邓丽君的父亲,帮她报名参加了“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比赛。
起初,邓枢瞧不上唱歌比赛,直到邓丽君打败五十几名参赛选手,拿到冠军,这才大喜过望。
邓丽君演唱的正是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访英台》。后来徐小凤、张国荣等人都曾唱过这首黄梅调。
得奖后,邓丽君跟随李成清的“康乐队”四处演出,每场下来赚得五块十块,可以补贴家用。
当时的邓家,生活可以说是窘迫的。听说加入天主教可以领到面粉、大米,邓丽君就加入了教会。邓丽君的英文名“Teresa”,就是在教会取的。
家里偶尔做一顿红烧肉,两个大不了几岁的哥哥总是让给妹妹和弟弟吃。
兄妹几个也做过不少“大事”,有一次,邓丽君跟着哥哥去偷番石榴,赤着脚踩到碎玻璃,血流不止,打了破伤风,家人才心安。
邓枢疼爱自己的女儿,见她唱歌有天赋,就经常带她去河边吊嗓子,一直到邓丽君的演出和学业多了才作罢。
邓丽君的功课,国文尚好,算数很烂。好在老师看重她是个苗子,经常帮她补习功课。
一九六五年,邓丽君进入台北金陵女中读书。后来,林青霞也曾就读于此。
△林青霞
邓丽君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去歌厅唱歌,一场演出下来大概一两千新台币,与台北普通职员的月薪相仿。
学校后来发现了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邓丽君放弃学业,正式出道歌坛,同年发行了个人首张黑胶唱片《凤阳花鼓》。
这一年,她十四岁。
邓丽君进入歌坛后,受到宇宙唱片公司的重视,到一九六八年底,已经发行了八张个人唱片,模仿邓丽君的打扮和唱腔,在台湾成为时尚。
同年,邓丽君受邀参加了台湾当时唯一的歌唱节目《群星会》。第一次登台,邓丽君就忘词了,这件事情也让她终身难忘。
节目组考虑再三,还是续用了邓丽君。
后来,她成为《群星会》的常驻班底。节目的制作人慎芝后来回忆,当时觉得邓丽君是个爱吃零食的小姑娘,尤其爱吃辣。
慎芝会写词,曾与凤飞飞、甄妮、蔡琴等人合作。一九八七年,慎芝还为邓丽君创作了《我只在乎你》。
至于吃辣还不伤嗓子这个问题,邓丽君说自己是“得天独厚”。
参加《群星会》之后,邓丽君经左元宏推荐,为台湾第一部电视剧《晶晶》演唱了主题曲。
这部催泪的电视剧,让更多的台湾人记住了这个“娃娃天后”。
一九六九年,新加坡总统夫人游莎夫突然向邓丽君发出邀请,希望她到新加坡去演出。
邓丽君的新加坡之行,为自己打开了东南亚市场。而同时期的歌手,还在台湾本岛销量榜上追赶她。
让邓丽君感到好奇的是,东南亚的饭菜口味与台湾类似,了解到当地有很多福建侨民后才恍然大悟。
这一年的冬天,应白花油药厂董事长颜玉莹之邀,邓丽君到香港参加《华侨日报》发起的“白花油之夜”义卖活动。那一晚,她募到了5150元港币,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白花油皇后”。
这是香港人第一次现场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四年后的一九七三年,邓丽君当选香港十大歌星,同期获选的还有徐小凤。
一九七三年,香港发生了不少事情。功夫巨星李小龙去世,歌手罗文开始走红,谭咏麟加入温拿乐队。
也是在这一年,邓丽君决定赴日本发展。
此前,邓丽君已经离开破产的宇宙公司,签约“乐风唱片”,左元宏成为邓丽君的唱片制作人,为邓丽君创作《千言万语》。
七十年代初,与左宏元合作过的欧阳菲菲、翁倩玉已经双双在日本发展,欧阳菲菲还凭借《雨中徘徊》获得NHK新人奖。
左元宏的合作歌手,总与日本有缘,这或许是一个巧合。
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从欧阳菲菲身上看到华语歌手的潜力,派出专员到香港物色新星。邓丽君一下子就被相中了。
专员听完邓丽君的唱片说:“她是台湾的美空云雀。”
美空云雀,何许人也?
美空云雀,原名加藤和枝,一九三七年生于日本横滨,九岁登台,十三岁前往夏威夷公演,一生演唱歌曲超过一千四百首,去世后被授予日本平民最高荣誉“国民荣誉赏”。
△美空云雀
一九七三年,邓丽君在母亲赵素桂的陪同下到日本发展。
同年,她发行了个人在日本的第一张专辑《是今夜还是明天》。最终,印制的三万张唱片“没有卖完”,在销售排行榜上位列第七十五名。
初到日本的邓丽君吃不惯日本菜,体重一直在掉。她不陪赵素桂逛街,关起门来练歌。
赵素桂负责邓丽君的衣食起居,为她烧爱吃的中国菜,还请公司的工作人员做了邓丽君的日语老师。
邓丽君配得上“美空云雀”的称呼,是在一年之后。
△《空港》专辑封面
一九七四年,邓丽君发行《空港》,她放弃此前的创新,恢复了“邓式唱腔”。这张唱片的销量达到了八十万张,排名挤进前十五位。同年,邓丽君获得了日本唱片大赏“新人赏”。
日本唱片大赏,相当于中国的金唱片奖。
邓丽君曾承认,自己在日本的几年过得不如意,尽管她发行的唱片销量早已超过之前的欧阳菲菲等人。
自始至终,邓丽君都没有取日本艺名,还经常演唱《小城故事》等歌曲。
相比之下,邓丽君更看重香港,她邀请日本工作人员到香港为她筹备演唱会,地点选在铜锣湾的利舞台。
时期,利舞台主要用于表演粤剧。上世纪七十年代,无线电视台开始在这里举办“香港小姐”决赛。
这场演唱会,邓丽君没有酬劳。
之后几年,邓丽君在日本、香港频繁开演唱会,在台湾签约唱片公司,并将演唱会收入捐作慈善基金。
一九七七年开始,两年间邓丽君先后发行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又见炊烟》。
好景不长,一九七九年,“假护照事件”发生了。
从始至终,邓丽君一直坚称:“护照是真的,是我委托朋友办理的。”
事情要从那年的二月十三日说起。
当天,邓丽君乘坐“中华航空”班机从香港飞抵台湾,准备立即办理飞日本的手续时,发现当天飞日本的航班已经客满。
邓丽君可以选择在台北留宿一晚再去日本吗?
按照当时的规定,因为邓丽君的台湾护照在此前一个月内已经办理过一次过境,她不能再以过境的名义在台湾停留。
日本公司方面正等着她去录音,邓丽君无奈之下问机场工作人员:“可以使用外国护照办理过境吗?”
说着,她拿出了整个故事的主角,一本印尼护照。
工作人员以“护照上没有台湾签证”再次拒绝了她入境。
邓丽君,一个台湾人,就这样被迫从台北返回了香港,另做打算。
此事并未就此结束,相反是刚刚开始。
邓丽君在台北机场的遭遇,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为了求证那本印尼护照的真实性,有人抄下护照号码,并给印尼“驻台湾代表处”打去了电话,称护照是伪造的。
十五日,印尼外交部紧急联系日本,将这一情况进行了通报。
十六日,已经身在日本的邓丽君,接受了日本会同印尼方面的询问。她承认了使用“印尼护照入境”,并表示对护照的真实性负责。
事关日本、台湾、印尼三方的关系,邓丽君又是知名歌星,谨慎考虑后,日本方面选择对邓丽君采取了“留置”措施。
所谓留置,限制人身自由是肯定的了。
那段时间的邓丽君经历了流泪到平静的过程,各路记者也在留置地点外观察事态进展。
二十二日,在邓丽君被留置一周以后,日本方面在与印尼方面调查核实后宣布:邓丽君所持护照及护照上的官方签字都是真的,但“取得程序不合法”。
二十四日,日本法务省裁决将邓丽君“驱逐出境”,一年内不得再次入境。
随后,邓丽君离开日本,直接赴美国读书。“假护照事件”就此结束。
邓丽君选择到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方面已经把她的行为定性为“背叛”。
到了美国以后,重新拾起未完成的学业,在洛杉矶做了两年学生。
五弟邓长禧当时也到了美国,他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的邓丽君喜欢穿牛仔裤,看起来却一点也不普通。
有时候,她会独自在房间里默默流泪,邓长禧就撞到过一次。
传言,邓丽君的护照是一位富商朋友托关系办理的。直到最后,邓丽君都没有供出这位朋友是谁。
一九八〇年三月,邓丽君没有被遗忘,她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女歌唱演员奖”。获得“最佳男合唱演员奖”的是刘文正。
△1981年,第16届的台湾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上,邓丽君、三毛和高凌风站在舞台上
邓丽君接受经纪人的建议,开始为复出做准备。随后的一段时间,她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华人聚集的城市举办了多场演唱会。
同年,邓丽君又在香港利舞台开演唱会,并发行了个人首张粤语唱片《誓不两立》。
至于台湾这个伤心地,邓丽君曾说:“除非邀请,否则我不会再回去。”
一九八〇年,邓丽君受邀担任台湾金钟奖颁奖礼的主持,并到高雄等地进行《何日君再来》演出。
在台湾,她见到了分离多年的父亲邓枢,分外欣喜。
刚成名时,邓丽君就用赚来的钱给邓枢购置了新房、汽车和西装。等到后来邓枢患病时,邓丽君回家探望,第一句话就用山东方言问:“老邓,你这是咋咧?”
回家的感觉很亲切,邓丽君发现台北变化很大,而自己的新生活也即将到来。
一九八〇年,邓丽君发行了《何日君再来》,人和歌,名字里都有一个“君”字。
这首歌描述旧上海生活的歌曲,又在日本大受欢迎,曾遭遇过误解,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其实,《何日君再来》出自一九三九年的香港电影《孤岛天堂》,电影讲述的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故事。
△《孤岛天堂》
从《何日君再来》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进入全盛时期。
一九八三年,邓丽君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唱十五场。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邓丽君连续三年获得日本有线大赏。
一九八六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全球范围的“七大女歌星”,邓丽君位列其中。
《甜蜜蜜》《小城故事》的词作者庄奴曾说:“只有一个邓丽君,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再有。”
庄奴、乔羽、黄霑被称为“华语词坛三杰”。
大陆的年轻人也很喜欢邓丽君,搞不到邓丽君的正版唱片,听翻录的带子也津津有味。后来,港台流行音乐正式引入大陆后,邓丽君依然是人们的最爱。
《甜蜜蜜》之所以很长时间内位居华语唱片销量榜首,大陆听众功不可没。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凌晨,邓丽君在新家坡刚过完自己三十二岁的生日,接到了一通远渡重洋的电话。
“什么,北京?”
当《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关键报上姓名,邓丽君很惊讶。她从未想过会有北京的记者给她打电话。
两人交谈甚欢,足足聊了五十三分钟,邓丽君在电话里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三、四年前我就听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有个美国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开始我半信半疑,后来,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心里很激动。我感激内地的青年朋友!”
邓丽君曾多次表示想到大陆演出,但她最终没有来到大陆。
央视第一次播放邓丽君的新闻,就是邓丽君的死讯。
一九九〇年,先是邓枢去世。邓丽君身在国外,因身体不适未能奔丧。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乙亥年四月初九,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因哮喘病突发,医治无效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但愿人长久,何日君再来。
部分参考资料:
《邓丽君画传》,师永刚 等著
《邓丽君全传》,师永刚 著
《环球人物》: 邓丽君逝世15周年祭:多名歌手翻唱其歌曲走红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姜捷 著
严歌苓散文:一天的断想
我回来了,从美国的秋天,澳洲的夏天,新加坡的春天,直接回到北京的冬天。结束了十个月的国外生活,或叫它访问、旅行、流浪都可以。
一切都跟着我回来了:创作时固有的生活习惯、生命状态、生物钟点。我的早晨是许多人的半夜。
很冷,暖气要在半小时后才会来。长久以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地道的笨鸟,除了头一个飞出林子别无指望。第一件事是关掉电话铃,到午饭前,无论火警匪警我都是浑然。我在十几平米的空间踱步,像那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上班的人,还像一头心事重重、尽量拖延不肯上套的驴。我极怕坐到那把椅子上,极怕拾起那支笔,就像多年前,我摸黑起床,匆忙梳洗,进了练功房却极怕换上舞鞋,极怕把腿搁上把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德行,一旦拾起笔,一旦穿上舞鞋,我就会把自己倾榨到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再也抡不动一下腿。
有时会鄙夷地问自己,这样惨淡经营地写出几部长篇小说,是否就很有道理的不孝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房间,不做饭,不听音乐,不去领免费但需排大半天队的军用罐头呢?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该写信了,该洗衣服了,该吃顿像样的饭了。
同时又懊悔得要命:在镜子前多站了几次;晚饭吃掉一小时,因为在会堂与人陷入了一个兴奋的话题;本来只看新闻却顺势看了个挺恶心的电视剧;原想学“托福”结果捧了本英文小说直读到睡觉。精打细算的一天时间全砸了,这个人貌似勤奋刻苦却仍是个浑浑噩噩的东西。每时每刻我都对自己有这样多的不满,搞得本来就孤家寡人的自己都很难与自己相处。
有人曾经跑来对我说:你呀,你知道你怎么回事吗?”他犹豫着,一面判断我是否吃得消他下面的话,“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太想出名!”
“对极了!”我立刻说。这倒使他意外了,使他的话一下子没了揭露性。接着我告诉他我从四岁就醉心功名。那时我的母亲常带我去参加一周一度的诗歌会,那是个云集着小城市大名流的地方。当一个著名诗人上场时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笑都显得可怜巴巴,每个人明明在捧场却都含着微量的敌意。当时我想,当一个大名人多么好啊,起码比当我父亲这样的中流名人要省力,因为一个中流名人暗里追求成功,明里却得追求淡泊,必须掌握大量哲理,摆出大量姿态,向自己和向别人否定这个追求,最终剩下的精力和时间只够让他位居中流。
一个美国青年对我说:“今天我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明天我有可能成功,这些成功的可能性里包括我被竞选为总统。”一个台湾少妇告诉我:“为了做一个最成功的太太,有时我都累得没有命了!”一个新加坡华人说:“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无数个人成功相加起来的。”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始终被教育着去尽量忽略个人成功,但面对着无论是相同人种还是不同人种,我都生怕讲不清。
写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件太偶然的事。编辑马马虎虎地约稿,我就嘻嘻哈哈答应了。但我心里却是十分当真的。至今我仍对任何编辑的约稿感到受宠若惊,包括那挡毫无诚意的。我所说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这事当真的编辑,他的马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过都是存心给自己留余地、留退路。这样我才认真干起来。什么事都是在你不知怎么干时干得特别顺手,三个月时间我就完成了《绿血》三十万字的初稿。这速度快得简直让我难为情。
我断定再甭想从自己脑子里榨出一个字的时候,才从椅子上站起来。什么都凉了,手、脚、血液,包括胸前绑着的大热水袋。虽然我把日历、钟表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午饭时间。
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但钱好歹还能储蓄。有时我甚至想,失眠就让它失吧,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但别人不同意,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所以我还是去睡。先是仔细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无,大汗淋漓。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这时,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当我把长篇小说稿扛到编辑面前时,只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种种病症,诸如突发性头痛,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出似的。交稿后,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我又是失眠又是头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若不成,我只有自杀去了。幸而它们都成了。之后,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流畅,结构之整体,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干、牛奶,阔的时候吃点水果。不能吃饱,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在美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你们就有希望了。”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心想这人有什么病。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我说当然。“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接下去,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但心里想,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等我挂上电话,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对我所具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我从不结交朋友,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我没有自信,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连续几天,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十九岁那年,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毫无指望地蹦啊蹦,我瞄准了,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直到我到了美国,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实在有些可怜。
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战国时的大夫们,若三个月闲居,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自己不被任用,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而是驱车出走,到别国寻求重视。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
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我写得极苦,这是个地道的“怪胎”,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以及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慰感情上有伤的母亲,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她一封像样的信。甚至她提出要来看我,也被我硬着心拒绝了。在这部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连去美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访问日期被我几次申请推迟。看见妈妈信上写:“年轻时,我以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我又总以为女儿会需要我,实际上,我始终在自作多情。”我为这些词句流泪,心里既烦恼又委屈。
当我从国外回来,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把这归结为聪明。我却说:“聪明是顶靠不住的东西。”我真的这样想,一个人最优越的素质是顽强、坚韧。只有顽强坚韧将如数报偿你所付出的一切:时间,精力,辛苦而枯索的整整一段青春。
记得有次我饿极了却找不出东西吃,就喝两包板蓝根。一时想起韩愈说的“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但愿我之辛苦不被人斥成活该;但愿有一日无数成功的个体相加成一个成功的民族。
天暗下来了。我也想歇下来,不阅读,不看英语,不做任何正儿八经的思考。想找谁聊聊天,想让谁用些散淡的话题来按摩一下我紧张得抽了筋的思维。然而我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在我需要别人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日子真的是很苦。我可以永远吃苦,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一九八七年18000元成交的“白发魔石”,专家:本是活物
作为奇石爱好者,很多人在早期的石展中都见过这么一方奇石:石头上长着浓密的“白发”,短的有5cm,最长的“白发”有10cm。最神奇的是据这方奇石的主人讲,这块“白发魔石”上的毛发一直在生长。这块奇石在前些年全国奇石展览会上也是大放异彩,屡次夺奖,但后来却在奇石展上消失了。那么这块奇石究竟是怎么来的?石头上的“白发”真的能自动生长吗?这些“白发”是真的头发吗?这块奇石最终去了哪里?
白发魔石
故事要从1987年说起,奇石爱好者田恩宏到青岛崂山出差,他有天在海边闲转时碰到一个卖石头的老人。吸引他的是这个老人面前摆的这块石头,远看就像一个巨大的猴头菇,唯一不同的是猴头菇是金黄色的,而这个是白色的。经过和卖石老人交谈得知,老人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石头,这是他在海边无意发现的,觉得稀奇就带了回来。田恩宏对这个奇石爱不释手,但也有些怀疑这些白色的毛发是不是用胶水粘在石头上故弄玄虚,于是转身离去。
白发魔石
离开后田恩宏并没有回宾馆,而是去买了一个放大镜,第二天他又来到卖石老人跟前。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白发”都是自然生长在石头上的,“发根”有一个个小黑点,确定是天然奇石后他开始跟老人讨价还价。卖石老人看他二次来到,知道他是真心喜欢这个石头,直接开价4万元。要知道当时的4万元可是天价啊,普通工人当时的月工资才是70元。田恩宏经过一番软磨硬蹭最终说好1.8万元成交,但是田恩宏身上并没有这么多钱,就给老人先交了一部分定金,回去想方设法凑齐了钱才算把石头拿到手。
白发魔石
田恩宏回到家后,妻子得知他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买了一个“破石头”,自然很不开心,然而事已至此,吵闹了几天也就由他去了。田恩宏小心翼翼地把石头摆到书房,整日把玩,但令他始终不明白的是,这石头上的“白发”究竟是什么东西。后来多次参加全国石展,也屡次获奖但遇到买家说什么也不卖,因为他想弄明白这个“白发魔石”的奥秘。刚拿回家的时候,这个石头上的"白发”还软软的,很柔顺富有弹性,后来无意发现这个石头上的“白发”还在生长,而且是中空的,点燃一头,烟会从另一头冒出来。
白发魔石
没想到三年后这个“白发魔石”上面的“白发”不再生长了,这更激发了天恩红的探秘欲望。经过十几年奔波,却没有一个鉴定机构能给出明确说法。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朋友推荐他拿到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去试试。2005年10月经过专家们仔细取样研究,查询了世界上各种动物的有关文献,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块石头很普通,但上面的“白发”却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这种动物叫多管直板头盘虫,是一种新发现的海洋生物,常附着在石头上和贝壳上生存。前几年之所以生长是因为石头上的水分还在,到后来石头上的水分和养分不够了,就停止了生长。
白发魔石
“白发魔石”的秘密解开了,虽说在民间没有多少收藏价值,但这种新物种还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专家的劝说下,2005年11月田恩宏把这个“白发魔石”捐献给了中科院研究所。头盘虫是一种管状的古老生物,以海洋微生物为食,也就是大家看到的一根根“白发”。这块奇石目前是海洋研究所的馆藏标本,一个奇石爱好者无意揭开了一个新物种,也算是对我国的海洋研究做出了贡献。如果您常在海边捡石头,也许有一天也能捡到“白发魔石”。我是石痴惠子,弘扬我国奇石玉石文化,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留意关注。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10-06有效身份证(2022年有效的身份证号码和真实姓名)
- 06-23陈建霖(陈建霖灵武市人民医院)
- 10-04法国啄木鸟剧情(看看真正的绿茶是怎么样的)
- 06-25泛民(你们还想选吗)
- 06-24孙秀芹(孙秀芹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 06-24蔡勤(上饶市广信区人民医院)
- 10-07汀读音(汀什么情况下读ding)
- 10-10江苏靖江十大特产(江苏靖江的特产是什么)
- 06-23鬼最怕什么(中国民间传说)
- 09-30海淀区是几环(海淀区在北京属于几环)
民俗风俗最新文章



- 01-23一九八七(一九八七属什么生肖)
- 01-23九划的字(九画的字有哪些字)
- 01-23撒贝宁身高是多少(撒贝宁身高是多少厘米)
- 01-23木肖有哪些生肖(五行木肖有哪些生肖)
- 01-23张氏头像(张氏头像男生霸气)
- 01-23泰府名邸(泰府名邸二手房)
- 01-23地母经(地母经原文)
- 01-23杨柳木命是贱命(杨柳木命是贱命 分析什么是杨柳木命)
- 01-23正月可以结婚吗(农历正月可以结婚吗)
- 01-23升卦(升卦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