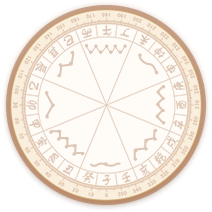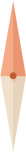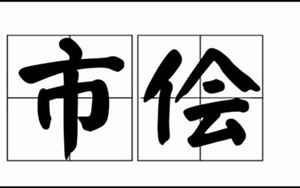梦见掉了三颗牙

认亲之后:“被拐者”王永福的人生下一站 梦想搞个白事礼仪队
回家只是第一步,更现实的问题是,即便拥有了合法身份,这个早已错过文化教育和家庭教育的26岁青年,下一步的出路将走向何方?
2019年5月14日,四川崇州市三江镇王桥村,王永福和阔别19年的父亲相拥而泣。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文|新京报记者 杜雯雯
编辑|胡杰 校对 | 刘军
看到父亲的第一眼,王永福强忍着的情绪一下绷不住了,他喊出一声“爸爸”,父子俩相拥而泣。好几分钟的时间里,两人说不出一句话,只听见喉咙哽咽发出密集的换气声。
为了这一刻,王永福等了19年。
他是一个丢失的孩子。8岁时王永福被人从家乡拐走,后来四处流浪,变成了“黑户”。
凭着对“家”的模糊意识,成年后的王永福曾多次寻亲,但都无功而返。
4月11日,新京报报道了王永福等人的寻亲故事(“黑户”寻亲者:像影子一样活着)。在警方和公益志愿者的帮助下,王永福终于和父母DNA比对成功。2019年的初夏,他回到了位于四川崇州市王桥村的家,看到了记忆中无数次出现的老家印象:土屋、晒坝、竹林、蜿蜒的小路……
在那间保持着40年前模样的破旧祖宅中,父子俩尝试续上中断多年的亲情。但有些情绪需要时间才能消解,比如王永福多年积攒下的委屈和对父亲早年恶习的埋怨。
“小时候我恨我爸,他经常打我,我也因为挨打才走丢的,现在恨不起来了,挨打也比流浪好。”王永福说。
回家只是第一步,更现实的问题是,即便拥有了合法身份,这个早已错过文化教育和家庭教育的26岁青年,下一步的出路将走向何方?
回家
四川崇州市东南隅的王桥村从没这样热闹过。
5月14日上午十点多,村民早早站在通往村委会的水泥路两旁,村口的猪肉铺、小卖店都聚集着一拨一拨的人。
村委会院坝搭起一个铺着红地毯的舞台,上面红色的条幅写着:欢迎回家。
王永福有些紧张,从当地派出所专门送他过来的警车里下来,他两只手不自然地抓着衣角下沿,从闹哄哄的人群中穿过。
姑姑和幺叔捧着两条红绸布先奔了过来,哭着给他交叉绑上,“幺儿(四川人对晚辈的爱称),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看到父亲的第一眼,王永福强忍着的情绪一下绷不住了,他喊出一声“爸爸”,父子俩相拥而泣。好几分钟的时间里,两人说不出一句话,任凭眼泪横流,只听见喉咙哽咽发出密集的换气声。
2019年5月14日,四川崇州市三江镇王桥村。认亲仪式上,王永福和父亲跪着相拥而泣。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一份由四川省公安厅打拐办公室公布的《被拐/失踪儿童身份确认通知书》证实了父子俩的血缘关系:通过DNA亲缘关系比对,确认被拐儿童家属王长根和干秀明夫妇,与被拐儿童王永福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
早在进村前的几小时,就有好几位村民在镇上认出了王永福,他们都记得这个小时候在村里到处跑的调皮孩子,“哎,你是不是王老幺哦!对,就是!”这是王永福的小名,村里人以前都这么唤他。
按照当地风俗,回家先祭祖。王家人陪着王永福先后去爷爷、奶奶和二叔的坟前上香烧纸。每次跪下,王永福都重重叩头,好几回头发都扎进纸灰中。
儿子回家后的第一顿饭,王长根特意请来厨子在屋门口摆坝坝宴,每一桌都是20道菜加一份汤,各式肉类鱼鲜占了三分之二,一层摆不下就叠起二层,这是农村宴席的最高规格。
父亲带着儿子一桌挨着一桌敬酒。每一次端起酒杯,王永福都会收到同样的祝贺词,“欢迎回家!”
进村和进家门时,都有一挂鞭炮炸响,他被包裹在烟雾中——在外漂泊时,别人最期盼的过年是他最难熬的时刻,他也憧憬窗外团聚和喜悦的烟花,便用烟头在自己手臂烫出一个个烙印。
儿子丢失后的日子
送走所有客人,一天的热闹散尽,直到深夜王家老宅才安静下来。
在两千余口人的王桥村,王长根这套建筑面积54.1平方米的灰色空心砖房算得上是最破旧的。
附近的亲戚邻里大多盖起新房,外墙贴着白色花纹瓷砖,小院儿用水泥抹得平平整整,养花种树,条件好的人家门前还停放着私家车。
只有王家还保留着四十年前的模样:屋顶起支撑作用的木梁和竹片已腐朽变形,防水主要靠瓦片下压着的那层红蓝条塑料布;堂屋也是厨房,做饭、待客都在这间;卧室墙壁灰得发黑,半米高的墙皮剥落,留下一条一条的水渍;一张褪色的花布钉在窗户上,充当了窗帘的角色,整个屋里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家具。
儿子在外受苦漂泊的这些年,王长根的日子也没好过到哪里去。
老汉今年56岁,但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即便剃成短短的寸头,也没能藏住近乎全白的头发。他皮肤晒得黑红,额头和眼角的皱纹又深又密,身材干瘦有肌肉,都是常年在外靠劳力吃饭留下的印记。
年轻时他炒得一手好菜,哪家有红白喜事他便上门去帮厨做饭。他还曾在镇上中学谋得食堂厨师一职,后来查出乙肝,办不了健康证也丢了工作。
王长根只能去工地和砂石厂打小工。一年中将近10个月他都在外面,崇州附近的双流、华阳、彭州他都去遍了,最远的一份工是在300公里外的阿坝州马尔康市。
两年前,病痛也找上了门。王长根发现腹部莫名发胀,不吃饭肚子也总是鼓鼓的。去医院才知道自己得了肝腹水。九个月的治疗花了近万元,王长根没有医保也没有积蓄,连看病的钱都是最小的兄弟帮着凑的。
王家亲戚将王长根穷困孤独的生活归因于他年轻时的恶习,“一天三顿都喝酒,脾气也暴躁,娃儿也打,老婆也打。”王永福两岁多的时候,王长根便和小四岁的妻子离了婚,至今没有任何往来。这次认亲,王永福的母亲也没有出现。
2000年的一天,他酒后动手打了王永福,孩子从家里躲出去。那天晚上,他曾寻人到晚上12点。又过了几天,还是没等到儿子回来。
刚开始,他以为男孩子调皮,肯定是跑到哪里玩了,便没当回事。直到他彻底失去儿子的任何消息,才真正意识到,孩子是真丢了。
2019年2月26日,上海,王永福在提起当年在北京站时所认的姐姐对他如何好时,流下眼泪。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王长根只读过小学一年级,外面世界互联网科技的发达与他无关,他不会上网,玩不来智能手机也没有微信。在他对于距离长短的理解中,三五百里路已经是他寻人的能力极限,“太远了怎么找得到,硬是寻不到就算了。”
后来,他打工时在电视上看到别人寻亲的新闻,便开始想象儿子是不是有一天也能自己找回来。王长根说自己从未想过儿子是被人贩拐走的,只在心里期盼,“只要不犯法,哪怕无业了要饭也可以”,这是他的最低要求,“进公安局的‘笼笼’就不行了,犯法要坐牢的。”
这些年里,他时常在夜里流泪,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想他,啷个不想他嘛”。在马尔康打工的时候,他曾连续两晚做梦,梦到永福回家。
即便如此,这位父亲还是没有选择报警——在他有限的认知范围里,他以为报警找孩子是一件需要自己掏钱的事,他没有钱。
五年前,王永福在一家公益寻亲网站做了寻亲登记。后来在公安局采了血。
之后的三年,王永福的寻亲路仍旧没有新头绪。直到2018年6月,王永福前往四川达州,找到当地电视台录制寻亲节目,随着寻找范围逐渐扩大,王永福的寻亲图片也散播到了崇州市三江镇的王桥村。
事实上,王家亲戚中,最先识别出王永福的是幺叔王正清。他看到寻亲的图片信息后,主动联络上公益寻人平台的志愿者和警方。同年6月,王永福疑似父母在四川省公安厅采血。几个月后,王永福与疑似父母DNA比对成功。
2019年2月27日,上海,王永福展示自己身上的一块记,希望这个也是认亲的线索。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崇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扫黑中队队长李祥吉,也是这次王永福回家手续的主要经办人。他坦言,正是由于王长根多年来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导致警方在排查时难度增大,找不到匹配的丢失孩子家庭数据记录,也成为王永福长大后寻家不得的直接原因。
人回来了,奶奶却不在了
今年2月,在接受《新京报》关于“黑户”群体寻亲的采访时,王永福曾描述过自己幼年对于老家的印象:土屋、晒坝、竹林、蜿蜒小路、坟包,还有收藏各种石头的邻居村长。
记忆中,家乡的农作物有油菜、水稻、玉米、橘子,饮食习惯是大米、辣椒和花椒;赶集时,会通过一座很长很长的老桥,有十几辆车那么长,桥离家很近,走路就能到。
关于这些生活细节的描述,王永福的记忆几乎完全准确。但一些最关键的个人信息,他却记混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他找到亲人的时间。
2019年2月27日,上海,在王永福租住的阁楼里,他拿着根据自己丢失前对家及家周边的情况画的示意图。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他所在的村镇隶属崇州,距离省会成都的车程不到一小时。
但在寻亲过程中,王永福向国内一家公益寻亲平台的志愿者提供的籍贯信息是四川达县(现在的达州)。三年时间里,多位志愿者跑遍达州的各大乡镇,几经排查也未能找到疑似家庭。
“不知道从哪儿听了一嘴达县,就记在脑子里了。”王永福回忆,或许是那时年纪小,听到拐卖的人贩说自己是达县人,便信以为真。他还记得家附近有一所名字中带有“柑子”的小学,但事后证明,崇州市附近并没有符合上述信息的地名。
类似的记忆偏差还有对父亲的描述。比如,在他印象中,父亲是几位叔伯中最小的一个,其实王长根在五姐弟中排行老三,是三个儿子中的老大。
比起父亲,一直以来,王永福最惦记的人是奶奶。他记得奶奶瘦瘦的,信佛吃素,总会在父亲发火时替他圆场,料理他的起居,只要看到他受委屈奶奶总是会问:“怎么啦,怎么啦?”
有一次父亲吊着打他,吊到手臂脱臼,也是奶奶一直帮着照顾。就连永福这个名字,都是奶奶取的。永福永福,永远幸福。
流浪时兜里最没钱的日子,王永福只能捡垃圾吃。他甚至想过自杀,左手腕上有他自己拿刀片割过的痕迹,幸好伤口没伤到动脉,逐渐愈合。没再次伤害自己,王永福说是因为“放不下奶奶”。
上个月,他才得知奶奶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心里那根绷得最紧的弦断了,疼得要命。那天晚上,他约着朋友喝白酒,把自己灌得大醉,一边喝一边哭。
这是他找到家后觉得最糟糕的事情,人回来了,奶奶却不在了。
也不都是坏消息,妹妹的出现就是惊喜。
王永福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生子。志愿者给他来发来两张妹妹的照片,他高兴得反复看了几十遍,逢人便展示基因的神奇:兄妹俩同是细长眼型,眼角带着弯钩,笑起来嘴唇两侧的弧度都像是复刻版。
这个小他两岁的亲妹妹,在父母离婚后便被抱养到别人家,两人并未有共同成长生活的经历。
“我回去之后我爸不会再揍我吧?”
与父亲见面前,王永福不止一次提到对父亲的恐惧和怨恨。
小时候,犯点小错误便会被棍棒教育,他被打怕了,以至于警方打来通知他认亲的电话时,他本能问出一句:“我回去之后我爸不会再揍我吧?”
他告诉警察,“要是再对我动手,我就和他断绝父子关系,绝对不会再容忍。”还放出狠话,要是再挨打,宁愿在外面漂着,死在外面也不回去。
得知家里第一个主动找到他的人是幺叔时,王永福更介意了,他心里有怨气,“怎么不是我爸?”他难过的是,自己在外拼了命找家,但父亲的寻子动作似乎温吞了许多。
他对父亲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暴脾气的嗜酒者,以至于见面后父亲的身体衰老变化让他惊讶:
身体差了,背也弯了,连性格都柔软了下来。多年不见的思念是真真的,埋怨委屈也是确切的,王永福自己也会挣扎在两种对冲情绪中。
王永福抓着父亲的手走在路上,大家都说爷俩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光是长相,即便分开多年,两人的诸多生活细节都保持奇妙的一致性。
住酒店时,王永福总是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挂好,室友的衣服随意搭在那儿,他也去帮人整理。王长根也是这样,家里没有衣柜,他干脆横起一根竹竿,两头用线吊在屋梁上当衣架使,衣服一件一件整齐罗列。
王长根床边有台笨重的收音机,能放音乐,这是他家里唯一的娱乐设施。王永福在上海的出租屋也有一台,只是款式更新一点。
大多数时间,父子间都是少语的状态,做事就做事,吃饭就吃饭。王永福性格外向些,是更主动展现情感的一方。重聚后,两个男人向对方表达爱和关心的方式都浅显直白:宁愿自己窘迫,也舍得为对方花钱。
王长根为儿子办的回家酒席花了九千六百元,他在外打小工一整年才能挣到这个数字。
2019年5月14日,四川崇州市三江镇王桥村。王永福正在给前来道喜的亲朋敬酒。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他对自己从没这么大方过。他曾花600块钱买了一台二手拖拉机,帮别人耕田维持生计。但生病后他找人借钱买药,便原价卖掉拖拉机,换回的钱刚好够还债。
他没主动提起这件事,是王永福在猪圈里发现了一瓶没用完的拖拉机机油,开口问了他才说。沟通,是他们都不擅长的事。就像王长根看见儿子手上的伤疤,他不敢主动问,他以为是开水烫的或是在外挨了打。
认亲后的第二天,王永福带着父亲到镇上置办行头。新买的手机是OPPO,衣裤鞋子是海澜之家,都是镇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品牌。
半天时间,王永福给父亲花掉了四五千元,这是他在上海打工一个月的薪水。王长根全程跟随,听凭儿子安排,他虽然话不多,但脸上看得出是高兴的。
每到一家店,儿子都让他挑个中意的,他先问价钱,“这个贵不贵?”王永福脸上红通通,眼睛眯成两条长缝,边笑边说,“哎呀,今天你别管钱,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王永福还特意花了1000块添置了一张1.8米的双人大床,配上素雅的蓝格纯棉四件套,计划未来一个月与父亲同住。这一刻,王永福似乎忘记了,就在见面前一天,旁人和他提到要不要与父亲住的事,他突然恼了,声调提高,拧着脖子语气强硬,“住不了,永远住不了,我可以认他,但不会和他住!”
自打父子俩见面时的那个紧密拥抱起,那些不愉快似乎被温情暂时遮掩住了。
人生下一站
当“黑户”的时候,王永福找不到好工作,大多都是别人不愿干的,他没得挑,想着能养活自己就行。
他的职业经历遍及大江南北:在北京的火车站帮人扛包、在石家庄替人开车、在广东的沙滩上给游客开游艇、在杭州的裤子工厂搞加工、在上海的游乐园倒腾门票。
其他孩子都在上学的年纪,他已经开始在社会上闯荡。错过了基础教育的机会,至今他都不识字。他和人聊天只能语音不发文字,朋友圈的内容也大多是复制粘贴。
5月14日下午,王永福前往崇州市公安局大厅补录户口。从小到大,正因缺少户口和身份证明,他遭白眼受欺凌,再委屈也不敢报警。打工时碰上黑心老板,知道他没证件,故意压着工资不发,逼到他走为止。
像王永福这样的成年“黑户”要合法拥有一纸户籍的手续繁杂:警方笔录、地址证明、DNA身份比对确认书、家庭房产证明。警方为他开了一个绿色窗口,在层叠码放的材料前,王永福在等待属于他的身份。
录完指纹,他到旁边的房间拍摄证件照。王永福脱下外套,端坐在一张小黄凳上,两腿张开,双手规规矩矩平放在两侧膝盖,像个学生模样。
2019年5月14日,崇州市行政审批局。民警正在给王永福拍证件照,用来办理身份证。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16时45分,他拿到了朱红色封皮下的那张浅绿色卡纸和一张临时身份证。那些曾经的颠沛流离正式宣告结束。
王永福交往过几个女孩,但最后都无果。他知道原因,“给不了人家什么幸福,用北京话说,一个臭盲流子能干什么,要房子没房子,要车子没车子。”
他抽烟抽得凶,一根接着一根,一包烟没多久就空了。生活的苦吃多了,连吃药他都不觉得苦,他去店里买了感冒药,扔进嘴里干嚼,药碎就着矿泉水咕噜噜吞下。
认亲之前,他只要管饱自己的胃。眼下,他想着要去找一份正当职业,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但到底怎么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他也想不出什么门路,念叨着,“只要是正规工作,酒店服务员也行,保安也行,先加油努力挣钱。”
他也有自己的梦想,比如搞个白事礼仪队,吹吹打打送人最后一程。他想着自己小时候还跟着父亲去殡仪馆帮逝者换衣服,不害怕也不忌讳。但算来算去,这个成本开销也大,他暂时还负担不起。
这趟回来,眼看着自己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小伙心里憋着一股劲。他想着,更得好好干了,等有钱了翻修老宅或是去崇州市里买一套小小的房子。
下午六点,天气突然转阴,落起大颗大颗的雨点,又急又密,敲得老房的瓦片劈啪作响。王长根进屋,弓着腰在屋内的土灶上给儿子做饭。
昨天宴席剩下的卤牛肉和猪耳朵在电饭锅蒸格中热气升腾,凉拌鸡从冰箱里拿出来就能吃,他还特意下厨煎了一大盘焦香的虎皮青椒,都是四川人餐桌上的家常菜。这张70公分的四方小红桌迎来了第一顿严格意义上的团圆饭。
2019年5月15日,四川崇州市三江镇,王永福家。晚上,王永福的父亲烧了几个菜,正准备吃饭。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也就一刻钟,饭菜端上桌子的时候雨也刚好停了。水珠顺着屋外的三棵皂角树滴落到地面,滋养着院坝上的一层松软青苔。
儿子不在家的时候,每到农历新年王长根总会买上一副新对联,贴在堂屋大门两侧。这个初夏的雨后傍晚,对联上的字终于变得应景:合家团圆贺新春,满堂欢乐迎富贵。
猜你喜欢
梦见掉了三颗牙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6-13八字食枭劫(枭印夺食是什么意思)
- 06-28卯兔怎么读(卯兔什么意思)
- 06-13八字比财食(食比财是什么意思)
- 06-17八字水和火多(八字里水火比较多是什么意思)
- 06-14双戊戌八字(八字带戊戌的人)
- 06-21八字鬼门官煞(八字鬼门关煞什么意思)
- 07-04吊梢眼(什么是吊梢眼)
- 06-12命格八字较弱(命弱的人有什么特征)
- 06-28梦到鹅(梦到鹅征兆好不好)
- 07-01己癸辛八字(丑中的藏干为什么是己癸辛)
六爻排盘最新文章



- 10-03梦见掉了三颗牙
- 10-031946年属什么(1946年属什么生肖几岁)
- 10-03梦见别人送饭给自己吃(梦见别人送饭给我吃有什么预兆)
- 10-03梦见自己买鞋(梦见自己买鞋试鞋是什么意思)
- 10-03怎么取名字(怎么取名字对宝宝一生有益)
- 10-03戊戌日柱女命(戊戌日柱女命看配偶)
- 10-03梦见别人送我钻石(梦见有人送我钻石代表什么)
- 10-03龙和牛属相合不合(龙和牛属相合不合财运)
- 10-03马字五行属什么
- 10-03聊八卦(聊八卦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