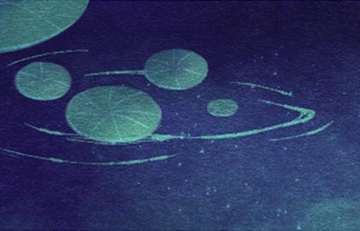南真

本文目录一览:
湘江周刊·封面丨山高人为峰——丽泽千年的城南书院
颜蒹葭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
多材自昔夸熊封。
学子努力,蔚为万夫雄。
这是一首校歌,从历经千年的城南书院唱起。
这是一首校歌,唱出了湖南第一师范的豪迈。
很多人知道,誉称“百年师范”的湖南第一师范是一代伟人的母校,一所涌现了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李维汉、杨昌济、徐特立、孔昭绶、易培基等一批革命家、教育家的名校,一个闻名中外的红色圣地和网红旅游打卡地。
可很多人并不知道,誉称“千年学府”的湖南第一师范,始于南宋宰相张浚和理学大师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一所在清代前期就成为全国二十三所、湖南两所省会书院之一的书院,一所成为近代湖南五大人才群体摇篮的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乔育平 摄
1.“必有其原因”
其实,我以前也不是很清楚。二十多年前,我在长沙市天心区委办公室工作。那时的区委区政府大楼就在南门口不远处,距湖南第一师范城南书院校区只有一公里路程。我多次因公经过学校门口,但始终不曾进去过。也许是因为跟许多人一样,当年对学校的辉煌历史和厚重底蕴了解得不够多、不够深,心底的崇敬感和渴望感也就不够大、不够强。
后来,我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工作,才开始深入了解并很快爱上这所源远流长的名校。
也许是缘分,从毛主席倡办的湘潭大学毕业多年后,我来到毛主席母校工作,并开始了研究和湖南第一师范校史(含城南书院史)研究。通过研究发现:伟人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偶然的。湖南第一师范学子能成为世界伟人,就像其母校成为中华名校一样,不是无缘无故的。正如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题词所言:“伟人长于此,必有其原因。”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譬如,湖南第一师范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和开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名师熏陶和益友砥砺为“集合同志”打下坚实基础;科学的招生办学体制和积极的自身努力保障了选才与成才。显然,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湖南第一师范传承了城南书院“成就人材,传道济民”的优良传统,弘扬了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等共同孕育的湖湘文化,并以此培育了以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子。
在湖南乃至中国书院史、教育史上,在近代湖南崛起史乃至近代中国变迁史上,城南书院都是绕不开的传奇。
2.学府近千年
清代长沙妙高峰地舆图(见《城南书院志》卷二)
妙高峰虽说不高,海拔仅仅70米,但能名扬千秋,自有其妙处。据明崇祯时的《长沙府志》记载:“妙高峰高耸云表,江流环带,诸山屏列,此城南第一奇观。”
为体验高峰之妙,清代两江总督陶澍曾亲临此地,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长沙竹枝词》:“妙高山色画屏新,妙高山下水粼粼。多少游人不知味,出山何似在山真。”
如此妙处,作为书院办学之所自是上佳之选。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一代名相张浚(1097-1164)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潭州(今长沙),携子张栻(1133-1180)在妙高峰筑造了书院,并亲书院额“城南书院”。共有屋宇31所、基地园土26处,并辟有监院、讲堂和六斋(居业斋、进德斋、主敬斋、存诚斋、正谊斋、明道斋)。营造了“城南十景”:丽泽堂、书楼、养蒙轩、月榭、卷云亭集楼台堂榭之胜,南阜、琮琤谷、纳湖、听雨舫、采菱舟融自然山水之秀。还有东渚、咏归桥、船斋、兰涧、山斋、石濑、柳堤、濯清亭、西屿、梅堤等十大胜迹,美不胜收,让人目不暇接。
乾道三年(1167),时任城南书院山长兼岳麓书院主教的张栻,与从福建慕名而来的朱熹(1130-1200),在两大书院轮流讲学论道将近两月,成就了千古佳话“朱张会讲”。讲学之余,他们流连于城南书院各大美景之中,并留下了《城南杂咏二十首》和《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
可惜天妒英才,张栻48岁就英年早逝,归宿宁乡官山。在弟子胡大时以及再传弟子们的传承下,城南书院依旧弦歌不辍。
当大宋摇摇晃晃走到德祐元年(1275)的时候,忽必烈的灭宋战打到了潭州城。城南书院堂室斋舍惨遭元兵焚毁,“十景”也几成荒芜。后来有人将南阜上的“苍然观”改为“高峰寺”,幸好张浚手书“城南书院”院额仍存寺内。
直到明正德二年(1507),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和湖南提学道陈凤梧提议恢复城南书院,但旧地已为吉王府所据。嘉靖四十二年(1563),长沙府推官翟台在高峰寺下建得学堂五间,但万历六年(1578)复废。
“道脉开南楚,朱张仰昔贤。”许多文人雅士甚为怀念,纷纷寻旧访古。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寻访后写下《怀张浚故宅》:“元臣矢庙算,力战绝和书。蜀道安磐石,平江返日车。亭台芳草合,池沼白蘋疏。弦诵留遗泽,承家仰硕儒。”
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谕令各省兴建省会书院。全国共建23所,其中湖南、江苏、广东、广西各建两所,其他省各建一所。尽管元明时期荒废许久,但城南书院还是与岳麓书院同为省会书院,并共享一千两帑金的膏火。显然,城南书院在经康熙年间(1714)生员易象乾等集资修复过后,雍正时仍有讲学活动和极高声誉。
但城南书院正式官方化并变得规制完备,是在乾隆年间。乾隆十年(1745),新任巡抚杨锡绂赴岳麓书院课试生童,但见肄业诸生寥寥无几,大失所望。得知士子畏涉湘江之因后,决定在城内都司旧署重建城南书院,以解决学子求学和官吏课试之不便。重建的城南书院有讲堂、斋舍、御书楼、礼殿等80间,讲堂上悬乾隆皇帝御准摹用的“道南正脉”匾额。御书楼藏书数千卷,中祀张栻、朱熹等。三十二年后,巡抚觉罗敦福不仅做了保护性修缮,而且将天心阁并入书院。
城南书院虽异地重建和官方化,但始终没有偏离创始人张栻确定的“成就人材,传道济民”宗旨。乾隆年间,城南书院的人才培养已与岳麓书院并驾齐驱。觉罗敦福称赞说:“先后读书城南者,亦多成业发名。人材辈出,收效亦与岳麓等。”
为“复前贤之盛绩,培昭代之人文”,巡抚左辅于道光元年(1821)在妙高峰旧地大规模复建城南书院,次年冬即成。复建后的城南书院有斋舍120间,藏书超万卷,“与岳麓书院巍然并列”。“城南十景”也全部恢复。妙高峰上还增建南轩祠、文星阁。从此成为全省招生的通省书院,内外学正、附课生额扩至138名,与岳麓书院相等。为示表彰,道光皇帝御赐“丽泽风长”。由此,城南书院步入鼎盛时代。
三十年后的咸丰二年(1852)七月,太平军占据妙高峰架炮攻城。长沙有幸成为太平天国唯一没有攻克的省会,但被太平军占据81天的城南书院堂室斋舍被毁,万卷图书和字画荡然无存。山长陈本钦等修葺之后,城南书院很快又人文日盛。
宣统二年(1910),长沙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抢米风潮。激愤的长沙市民与外地饥民两万多人捣毁米店万余家,捣毁抚署、税关、大清银行,焚烧外国教堂、美孚煤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日本洋行等。遗憾的是,官府举办的新式学堂也成了愤怒饥民们报复的对象。此时的城南书院已经改制更名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是官办的洋学堂,由此惨遭焚毁。
不过,卷云亭仍在,直到二十五年(1936)还在。创始人张浚亲书的“城南书院”院额也在,直到二十二年(1933)还在。但一个署名“西耕”的人,竟在《长沙新市政计划中保存之名迹》一文中胡说:这匾额乃“杀穆之嫌疑犯张浚所书”,应列为“不保存之列”。事实上,参与陷害岳飞的并非贤相张浚,而是奸臣张俊。作者学问不精,浚、俊不分。一篇不负责任的文章,毁了一件流传近千年的国宝级文物!
尽管城南书院的建筑化作了尘土化作了历史,但城南书院的优良传统融入了湖湘文化之中,传给了承继者湖南第一师范……
3.“君子六千人”
晚清时期城南书院图(见《城南书院志》卷二)
“物态凝眸而盎盎,千古灵区;弦歌入听以雍雍,一方雅化。”
城南书院的“雅化”从南宋开始,以理学“主打”。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成为“昔贤过化之地”“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对湖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个时期的最大功臣,无疑是世称南轩先生的创始人张栻。他早年从“卒开湖湘之学统”的大儒胡宏问程氏之学。胡宏赞之:“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后来掌教城南书院,又兼主岳麓书院,还在碧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盛极一时,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
张栻既是理学家,也是教育家。在办学方针上,主张以“成就人才,传道济民”为宗旨。在门生招录上,主张为国选士的精英教育。在教学程序上,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在教学内容上,强调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在教学环境上,以讲堂讲授为辅,以师生相从燕游讲习为主。在知行关系上,主张“知行并发”,认为“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反映在教学上即主张学为实用。在张栻掌教下,城南书院涌现了一批传承道统、匡济天下的英才。
据考证,城南书院山长张栻门人有17位:胡大时、胡大壮、吴猎、赵方、游九言、游九功、陈琦、方耒、潘友端、宇文绍节、范仲黼、范仲芑、钟炤之、张巽、曾撙、吕胜己、周奭。他们多为理学门派优秀子弟,半数以上中进士、有官职。张栻并不反对学生应举,因为有官职者能更好地“传道济民”,他只是反对“为举业而来,先怀利心”的唯功利论。
南宋之后,城南书院在元明两代走过一段曲折历程。清中叶异地办学时(天心阁时期),谭又新、吴铁夫、吴德汉、余廷灿、杨宗岱、陈士雅、朱声亨、罗畸、罗廷彦等山长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但主体课程仍是程朱理学和四书五经,侧重于《四书集注》等宋儒著作诵读。城南书院再次真正兴盛,是道光二年(1822)在妙高峰旧地复建以后。
战争后,一些开明山长倡行经世致用之学,城南书院学风由此大为改观。贺熙龄山长要求学生“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除了义理、考据、词章学之外,兼学经济之学,由此培养了左宗棠、胡林翼等一批经邦济世之才。左宗棠在城南书院收获甚大,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人生走向。郭嵩焘山长也进行了改革,教学内容重“实学”“时务”,授课方式以学生自研为主、教师讲课为辅,并设立会讲制度辩论争议性问题,由此培养了张百熙、瞿鸿禨等优秀门生。黄兴入读城南书院长达五年,先后从学山长王先谦、刘凤苞,学识大进。
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西学东渐的深入,书院教育面临巨大挑战。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城南书院学子宋璞等向巡抚陈宝箴提交了《请酌改城南书院课程禀》,希望将本院每月官课仿照经济特科增加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六门命题,山长馆课仍课四书文兼课时务。陈宝箴准其所请。随后,城南书院进行了课程大改革:第一,引入和增加新学课程;第二,增加算学和译学课程;第三,按新增新学分门课试。
在贺熙龄、陈本钦、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刘凤苞等山长掌教下,城南书院和着时代的节拍与近代湖南前进的步伐,形成了与近代湖南相一致的五大人才群体,即以李星沅、唐鉴、贺熙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樊锥、皮锡瑞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谭延闿、黎尚雯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黄兴、陈天华、杨毓麟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推进了近代湖南乃至近代中国的发展。
“燕柳最相思,身别修门二十载;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这是黄兴的老师、曾任湖北布政使的梁鼎芬撰写的武昌府头门联。也有人说,这可能是称赞城南书院的名联,因为下联用来形容城南书院实在是太贴切不过了。是的,确实贴切。
4.蝶变见奇迹
游客参观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罗汇芳 摄
《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走到了悬崖边上。为缓解统治危机,清廷开始实施新政。传统书院开始面临教育近代化的机遇和挑战。
清末书院改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顿、改良旧书院,第二阶段是另建新型书院,第三阶段是将旧书院改造为新式学堂,即要进行近代化改制。
湖南也加快了书院改制步伐。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巡抚俞廉三在长沙黄坭塅创办湖南师范馆及附属小学堂,任命王先谦为馆长。因王先谦当时仍为岳麓书院山长,多由其高足、历史教员颜昌峣代行其职。同年十一月,新任巡抚赵尔巽以黄泥塅馆舍狭窄、无法扩充学额为由,将湖南师范馆迁至城南书院,合并改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千年学府,至此蝶变,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此碰撞、激荡。
光绪三十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单独建立了师范教育体系。同年,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改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
次年八月,谭延闿被巡抚端方任命为学堂监督。他四年前还跟城南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刘凤苞学过作文,后来官至国民政府主席。在任期间,他修建南楼(礼堂),扩大规模,参照日本学制使学堂向教育转变。一年后,早年求学城南书院的刘人熙接任监督,后来一度做过湖南代理督军兼省长。他保持了前任的办学成果,并按学部《师范选科章程》的规定,改文科为历史地理科,改理科为物理化学科,并坦言支持学校实行教育。
1912-1913年,政府公布一系列学制改革方案,合称“壬子癸丑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学制。该学制规定,将学堂改成学校。于是,1912年、1914年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先后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书院改学堂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书院教育和传统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可取的。中西文化交流,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外一种文化,而是要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幸好,学校迎来了孔昭绶、易培基等开明校长,并聘用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一批进步教员。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将城南书院的优良传统、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与西方文化、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不断发展学校的教育,并使之开花结果。
是很幸运的,来到了拥有多位开明校长和诸多进步名师的湖南第一师范就读。
湖南第一师范也是幸运的,招到了“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有志青年。
对这些名师敬爱有加,并得到了他们的栽培。特别是“欲栽大木拄长天”的杨昌济,成为的人生楷模和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也是引导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领路人。杨昌济病危时还向章士钊写信推荐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来回忆说:“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同时,结交了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萧三、陈昌等志同道合的学友,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成立誉称“建党先声”的新民学会,形成了致力于新主义革命的新民学会派,为建党、建军、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改写了中国历史进程。他们彰显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道义担当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基因,既是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力注脚,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给养。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和社会实践,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1950年,与同班同学周世钊叙旧时深情地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岁月就像淌过的湘江水,一去不复返。而湖湘文化之精神,从宋代的城南书院开始就代代相传,川流不息。湖南第一师范先辈们在筚路蓝缕中求索,在苦难挫折中奋进,敢挽狂澜于既倒,敢扶大厦之将倾,涌现了以为代表的一大批历史风云人物。据统计,湖南第一师范入选最新版《辞海》的师生有57人,入选《辞海》其他版次的有2人,总共有59人入选《辞海》。其中,城南书院时期有17人,师范教育时期有42人。
记得岳麓书院大成殿悬挂着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是城南书院学子、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的名联,道出了湖南人的底气,喊出了湖南人的豪气。
城南书院,丽泽千秋;第一师范,谁与争锋?
于是,我亦撰联一副:
城南宛然浮玉,千载讲学胜地,古非师范今师范;
书院长与流芳,百年革命摇篮,我不第一谁第一?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6-22王俊凯八字妻星(王俊凯八字分析老婆性格)
- 06-27圣杯4正位(塔罗牌圣杯四正位代表什么意思)
- 06-29权杖二逆位(塔罗牌权杖二逆位代表什么意思)
- 06-21王俊凯的八字(国民男孩王俊凯紫微命理)
- 07-07节制逆位(塔罗牌节制逆位代表和象征什么含义)
- 07-05克妻怎么化解(如何化解克妻的四种方法)
- 06-19猫外八字腿(为什么猫咪会外八字走路)
- 06-251984年几岁(1984年属鼠的今年多少岁了)
- 06-282018年几岁(2018属鼠的今年多少岁了)
- 06-22八字自坐旺(八字自身强旺是什么意思)
生肖鼠最新文章



- 12-28南真
- 12-28互的结构
- 12-27龚施茜(龚施茜和龚慈恩)
- 12-27十句让男人最感动的话(十句让男人最感动的话生日文案)
- 12-27农部首(农部首是什么偏旁)
- 12-27狮子男超级喜欢射手女(射手女和狮子男谁更离不开谁)
- 12-27三弊五缺(三弊五缺是所有道士还是只有算命的)
- 12-27普彤寺
- 12-27做梦鞋丢了(做梦鞋丢了找不到是什么意思)
- 12-27变色蛇(变色蛇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