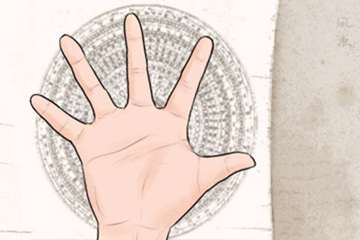横死的人会缠谁(如果一个人有了轻生的念头怎么办)

百年老宅为何有多人横死?难道是鲁班术?荒废多年竟还洁净如初?
前些日子的闲聊中,好友曾提起一篇在网上掀起轰动的文章,那大概是08年左右,有一些户外爱好者将无人居住的风门村称为‘鬼村’或‘封门村’,讲述了一些发生在里面的灵异事件。
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诡异现象?现实生活中就有许多老房子,只要还有人在里面生活居住,就算外表看起来很快就要倒塌的样子,可多年后,却依然生机勃勃,在风雨中坚挺。
那些高大宽敞,装修豪华的大房子,只要没有人在里面住,过个三五年后,四周开始慢慢长草,逐渐变得陈旧,最后坍塌,里面也是一派死气沉沉,毫无生气可言。
为什么有人住的房子,反而越住越新呢?没人的房子却越来越荒凉可怕?
聊到这里,我猛然间想起,我那乡下老家的旧宅院似乎并不是这样子,那简直是个例外般存在的怪物!
老院子里的家人,这些年逐渐有人搬走,到如今只剩下一座空空的大院子,守候在那个封闭的山坳里。可奇怪的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回去打扫的时候,却并不会觉得阴森可怕,反而有种一直有人在里面居住着的感觉。
老院子是建在三面环山的山坳里,前面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道长满灌木的悬崖,从远处看,只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那里还有人居住。
听长辈说,我们程家并不是修建这座宅院真正的主人。当初祖辈们为了躲避战乱,携家带口往大山里奔逃,在逃跑的路上,偶然间发现了一座被厚厚的野蔷薇藤遮挡严实的木牌坊........
那大概是初期吧,各地军阀混战,老百姓为了能够活下去,纷纷四散奔逃。程阿贵(我的祖祖)肩上挑着担子,一头的竹筐里放着一个两岁,一个四岁,还有一个不到一岁的三个小娃娃;另一头的筐里放着家里仅剩的粮食,身后跟着一双小脚的老婆,一步一拐跌跌撞撞的走在人群最后面。
漫天的黄沙,将逃荒的百姓从头到脚,全都染成土黄色,哭声,喊声,骡子声,夹杂在一起,闹成一片。路边的树叶,早被摘得精光吃掉了。不知是谁惊慌地大喊了一声: “有官兵来了。”紧跟着就听见鞭子在马背炸开了的声音,四散奔逃的人群立即引起一阵骚乱。
程阿贵连忙拽着小脚媳妇,领着一部分族人小心地避开跌跌撞撞的人群,往旁边的小道上走去,慢慢地越走越远,翻过一道道山梁,淌过数不清的河流,终于在几天以后,找了个稍微平坦的地方暂时安顿下来,打算等天亮后再继续寻找落脚的地方。
迷迷糊糊之间,阿贵隐约看见不远处有个影子在向他招手,似乎在叫他过去。他一时迷糊起身将怀中的儿子放在地下,抬脚就跟着那道影子追了上去。
也不知道具体走了多久,当他跟着影子翻过一道山梁后,眼睁睁地看着那道黑色的影子竟然弯腰钻进了一丛野蔷薇后就消失不见!紧接着耳边似乎有个声音说道: “这里是卧龙山腹地,带着你的族人住进来吧,以此远离战乱.......”
阿贵四下里看了看,到处都是黑蒙蒙的一片,连个人影子也没有,怎么会有人说话呢,肯定是自己听错了。他想往前再走走看的时候,刚抬起的脚,竟然一下子踢到儿子的小腿上,疼得孩子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这突然的哭声,将阿贵惊醒,他“腾”地一下子坐起来,看着四周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族人,不禁吓了一大跳。小脚媳妇也被他惊醒,赶忙坐起来把孩子抱进怀里柔声轻哄,有些担忧地问道: “怎么了?”阿贵长长地叹口气,摆摆手说没事,坐在那皱着眉使劲地回忆起梦里的情景来。
后来,大家跟着阿贵翻山越岭,终于到达卧龙山后山的时候,眼前正是梦中那道爬满厚厚野蔷薇的绿色墙!这时的蔷薇花早谢了,一层一层的枝叶紧紧地缠绕在一起,透过细微的缝隙,隐约露出一截陈旧的木头来,指甲盖长的黑色蚂蚁,延着蔷薇枝不停地来来往往忙碌不已。
“这里,就是这了,肯定没错!”阿贵有些激动地喊了起来。
阿贵抽出扁担,从蔷薇架下探进去上下左右一阵扒拉,很快就弄出一个可以容人进出的洞,他猫着腰率先钻了过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已经连成海的野蔷薇,一座半榻的大宅院,在野蔷薇的覆盖下昂首挺立着,廊下的柱子上、梁上还能看见一些掉了色的八仙画,兰花图来......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电话里传来老父亲有些哽咽的声音,你二奶奶走了。我在心里默默地为她松了一口气,低声说道: “她这样也好,也算是一种解脱。”
二奶奶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她是个个性很强又十分爱干净的老太太。她每天都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一头已经花白的头发,每次都梳得整整齐齐,在后脑勺盘起来插上一支檀木发簪,最后还要抹上一把铮亮的发油。家里不管什么事都要做在别人前面,绝对不能容忍落在人后。
就是这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小老太太,却在过完65岁生日的第二天晚上,突然变得疯疯癫癫起来。见人就骂,儿子也好,女婿女儿也罢,就连周围的邻居都骂。气得女儿女婿转身就回了自己的家。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以为二奶奶只是看不惯小辈们的某些行为,才开口大骂的。大家见着她的影子都躲得远远的,想等她气消了再来看她。可是二奶奶却在几天后变得越来越让人讨厌。
渐渐的,她不光骂人,还开始砸东西,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砸了个遍。砸完还不解气,又对着陪嫁衣柜上的穿衣镜,扭着老腰一件一件的把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看着镜子又跳又笑,完了就往外面跑。
到这个时候,儿子们才猛然醒悟过来,老太太这是得了疯病啊!儿女们强吼着给她穿好衣服,把鸡窝一样灰白的头发,给她梳整齐盘起来,用一条2米多长的黑色丝帕包起来,连夜开车把她送往市里的精神病医院。
等检查完毕后,医生说老太太是受了刺激得了失心疯。儿女们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等到确诊下来的时候,小女儿还是难以接受,双眼一黑,当时就在医院的走廊上昏了过去。
后来好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儿子女儿透过玻璃窗,看着二奶奶打了镇静剂后,斜躺在一张蓝色的小床上,双眼无神的看着窗外的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生无可恋,就那么定定地看着......
女儿实在是受不了,扑通一声跪在哥嫂的面前,求他俩把母亲接回去,大家一起想办法照顾。兄妹几人在窗外抱着大哭了一场,吓得住院部的医生护士连忙跑过来安慰。
第二天早上,二奶奶就被接了回来。儿子,女儿轮流着照顾,她要骂就骂好了,只要守着不往外面跑就是了。这一守就是大半年,大家也累得话都不想多说一句了。
昨天下了一场雨,让干涸的庄稼终于缓过神来,二奶奶将脸卡在长了铁锈的窗棍上,看着外面漫天的雨雾,突然咧嘴哈哈哈地大笑了几声后,笨重的身体往下一歪,倒在地上手脚不停地又挥又蹬起来。
等大家发现她的时候,二奶奶的身体都已经凉了半截了。
满院子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女们,在‘地仙’读长篇祭文的时候,不断传来低低的哭声和吸鼻子的抽噎声夹杂在一起。
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母亲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面带微笑地自言自语着什么......
母亲在她30岁那年,也正是在这所老宅里,因为一些事想不开,也得了这样的疯病,医生说这叫精神症,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治之症!
记得母亲时常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面带微笑的说着什么,就像有什么外人看不见的人在与她聊天一样。每当这种时候,我都吓得浑身发抖,时不时地凑到她跟前,一屁股挤进她怀里问她刚才在说什么,可每次母亲都会用手抱紧我,柔声说啥也没说。
可是几分钟后,她又对着空气聊天,说话......问题是我却一个字也听不清,也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我小时候极贪恋母亲的怀抱,即使是这样疯癫的母亲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害怕,我害怕的只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每当别人问起,你害不害怕你妈啊?我都很惊讶的看着她,说:“为什么要害怕?我妈好好的。”
大家都传母亲是因为娘家大哥的死因不明,受了刺激才让她的病情加重了些。
我大舅半夜肚子饿,从来都不待见他的舅妈,那天夜里竟然破天荒地给他煮了碗面条吃!可谁知道还没等到天亮,身强力壮的大舅说没就没了。后来,据说还被法医当场开膛破肚取走了内脏检查,几十年了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母亲作为他的亲妹妹,曾亲眼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
后来,母亲的病加重了,她不再守着家,开始背着她的所有衣服杂物,东躲西藏起来......于是,我也不得不开始一边念书一边翻山越岭地四处找她。
记得有一次,我去外婆家找她的时候,她正好与外婆一起在水井那洗衣服。可是等我和外婆刚晾上两件衣服,母亲就又从后门出去了。
我连忙跟上去,又喊又哭地问她要去哪里?她笑着说不去哪里。她也不等我,转身继续往前走,还是外婆赶上来,我俩才勉强将她拉了回来。
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母亲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又背着她的家当走进了黑暗之中......月初的夜晚,农村到处都是漆黑一片,从小就怕黑、胆小的她,竟然在那样的黑夜里健步如飞!
那天晚上,外婆家附近的所有人,都举着火把漫山遍野地找她,就连传说中的龙洞,大伙都爬进去找过,却连她的半个影子都没有见着。第二天早上,有人说在独角峰下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几件女人的衣服。
等我小心翼翼地爬上独角峰的时候,除了上面的草有被压过的痕迹以外啥也没有,就连所谓的女人衣服我也没有找到。我精疲力竭地躺在被压过的草丛里,委屈地哇哇大哭起来,埋怨母亲为什么要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折磨人。
母亲的病时好时坏,好好的时候,我曾问过她,为什么要离家四处躲藏。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家里到处都是奇怪的小人!
这些小人张牙舞爪地要来害她,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不许我母亲住。我不信,拉着母亲的手,非让她指给我看,小人在哪里?她指着泛黄的墙,指着陪嫁床上的白色蚊帐,说你看,你看啊,到处都站着小人,就连脚下的泥地上都有小人正在用手撕扯她的裤脚......
有时候夜里我和她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她半夜会突然坐起来,双手不停地挥舞,嘴里大吼道: “不许你们靠近我孩子......”我睡眼迷蒙地喊她,她才又安静的躺下,可却再也不肯闭上眼睛休息。
母亲终于在汶川地震那年的冬夜里突然走了。还没来得及让我见她最后一面,她就那么决绝地走了,再也不管她孤零零的女儿,再也不保护女儿,赶开那些诡异的小人......那年我22岁,成了别人口中名副其实的没有妈的孩子。
老宅子又一次热闹起来,是母亲走后的第三年夏天。爷爷翻完他晾晒在院子的草烟后,突然胸口疼的厉害,那一瞬间,他身上所有的衣服被汗水打湿,古铜色的脸变成了猪肝色。
后来确诊说是肝硬化(肝癌)晚期,让领回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好好照顾就是了。那一瞬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好几岁,呆呆地坐在老宅外面的木牌坊底下不停地抽烟。
老宅子在送走了爷爷后不久,大家正商量着过完年找人把它大修一次的时候,院子里的大娘却又出事了。
大娘这大半辈子,在外人看来至少是顺风顺水地过来:嫁给青梅竹马的爱人,生儿育女,没有婆媳纠纷,就这样过了大半辈子。谁知道,她却在知天命的年纪里,用三尺白布把自己挂在陪嫁过来的架子床上!
她走的那天,风夹着细盐似的雪粒子,呼呼地怒吼着,卷起地上干黄的树叶,忽上忽下四处翻飞......大家都围在院子西边的火房里烤火闲聊,任谁也没有想到,大娘就在黄昏的时候,让自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那天晚上,老宅子里灯火明亮,堂姐撕心裂肺的哭声响彻整个山坳。
就在大家忙着料理后事的时候,大伯却领着个女人,顶着漫天的风雪进了门。当时来帮忙的人都被大伯这一举动惊得愣在原地半天才缓过神来。
那个女人跟着大伯走进堂屋,想替大娘上香的时候,堂姐气红了双眼,腾地一下站起来,一把夺过女人手里还没来得及点燃的香,连人带香推了出去,厉声喊道, “滚出去!”
大伯连忙上前将女人护在身后,指责堂姐失了礼节。
就他这一句话,彻底将堂姐激怒,一把拽住她父亲的胳膊,拉到棺材旁边,指着里面躺着的大娘,让他看清楚,她娘是怎么死的。大娘原本清丽的脸上,一片青紫,肿大发紫的舌头怎么也收不回去!
堂姐怒目圆睁地盯着大伯,等他爹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场面一度混乱起来,堂姐和那个女人不知什么时候扭打在一起......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大伯大吼一声后,上前狠狠地给了堂姐两耳光。父女俩就在大娘的棺材旁边大闹了起来,邻居们连忙上去将俩人分开,各自劝说一阵。堂姐大哭着不停地拿自己的脑袋往棺材上撞,幸好大家及时拉住了她,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父女俩也因此断绝了关系,不再相认。
多年后,堂姐的儿子结婚,大伯都不曾参与。如今,听我爸说,大伯也被诊断出得了肝硬化,恐怕也时日无多了,只是不知道他心里可曾有过一丝丝的后悔?
这就是在那座老宅里上演的一幕幕真实的人间闹剧......
老宅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斑驳,木制的牌坊也逐渐变成朽木,只有那些蔷薇花,默默地开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见证了程家的悲欢与离合,也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突然离世的男男女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慢慢地从老宅里搬走,到如今它已经空了十多年了吧?只是偶尔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仍然住在那个陈旧压抑的老式大院子里,任凭你怎样挣扎,都逃不出它的高大围墙......
这次放假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老宅!
看着爬满牌坊的蔷薇藤上,一朵朵洁白的蔷薇花,在阳光下怒放;风吹过,带起阵阵醉人的花香。
推开紧闭的大门,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期间有一小丛不知名的小野花,在墙根努力绽放。凭着记忆打开母亲的婚房:阴暗的房间里,隐约有一股发霉的味道,阳光从护窗照了进来,在昏暗的房间里形成一道道暖黄色的刺眼光柱。
光柱里有浮尘在上上下下不停地漫游着,发黄的白墙上,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一些黑色的污渍,在余光中慢慢地居然幻化成一张女人的脸来......
她抬起星眸看着我微微一笑,红唇轻轻翕动,似乎在说着什么,我侧耳细听,却又什么也没有,可我明明看见她双唇轻启了啊?
我抬脚往前走了两步,想要看清楚些的时候,墙壁上除了一片发黑的污渍以外却什么也没有,刚才的女人脸难道是我看花了眼?正当我犹疑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冷冰冰的话语声。
“当年把院子借给程阿贵和他的族人住,是需要用同等的东西来交换的,当年是我给了你们庇护,这些年你们却将当年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既然如此,那从现在开始,就还给我吧!”
陌生冰冷的声音,忽然又变成母亲温柔的嗓音,一声一声的叮嘱,在耳边响起。
一只黑色小猫,从门口急速地窜了过去,我浑身一个激灵,瞬间清醒过来,看着房间里熟悉又陌生的一切,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老宅已经好几年没有人住了,虽然院子里长满了杂草,可房间里的家具上,却并没有落下多少灰尘!我打开老式的衣柜,发现柜子里还有母亲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枝干枯的白色蔷薇花,安静地斜躺在上面。
我转身跑到别的院子,一把推开大娘当年的那个房间,房间里依然光洁整齐,妆台上的铜镜旁边,有一支点缀着白玉的银钗,钗身上光洁明亮,似乎刚从女主人的头上拔下来,放在妆台上的。
院子里似乎到处都透着古怪,走廊里彩色的图画有些斑驳褪色,有些地方却像刚被人打扫过一样,我跑遍老宅所有的房间,全部打开门仔细地看了一遍,不禁惊得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浑身被汗水浸透......
现在的农村到处都是无人住的旧宅,几年过后,好好的房子变得荒凉不堪,比人还高的杂草从碎了的玻璃窗里探出脑袋来,墙根上的老鼠洞越来越多,那些木制的老宅院也越来越少。
我家的老宅却一直神秘的存在着,冥冥之中似乎有人在时刻维护......不知道在历史的洪流中,它最终将走向何方,也不知道这座隐藏在大山里的宅院,多年以后又会被冠上哪一个姓?......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精选
- 06-13八字怎样修印(八字如何补印)
- 06-29牛和龙属相合不合(属龙和属牛合不合)
- 06-13八字排流年盘(八字如何排盘)
- 06-24上升金牛(上升金牛座是什么意思)
- 06-291997年多少岁了(1997属牛的今年多少岁)
- 06-25金牛座有什么特点(金牛座的十大特点)
- 06-2997年几岁(1997属牛的今年多少岁)
- 06-10八字戌看性(戌土代表什么)
- 06-23梦见牛攻击自己(梦见牛攻击自己是什么意思)
- 06-25牛多少岁(属牛今年多大年纪)
生肖牛最新文章



- 01-15横死的人会缠谁(如果一个人有了轻生的念头怎么办)
- 01-15三月出生是什么星座(四月出生是什么星座女)
- 01-15巨蟹座男生配对星座女(巨蟹座男生配对星座女水瓶座)
- 01-15能让白羊男回头的女孩(和白羊男分手后还有可能复合吗)
- 01-15四月十三(四月十三日是什么星座)
- 01-15鲁班尺最吉利尺寸大门(鲁班尺最吉利尺寸大门3米里最吉利)
- 01-15什么送爽(什么送爽四字成语(秋天))
- 01-159524开头是什么电话(0229524开头是什么电话)
- 01-15狗能看出人的气场(狗狗死了最好的处理方法)
- 01-152.20什么星座(农历12.20什么星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