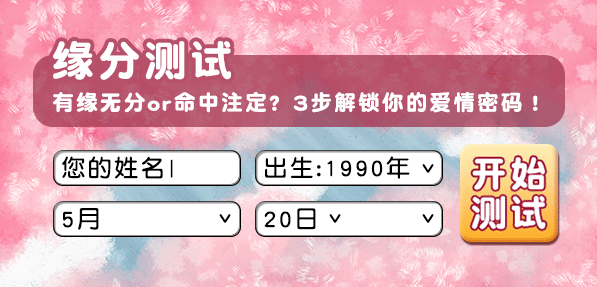217是什么意思(217是什么意思爱情含义)

刘文 蒲江林 ‖ 梓潼由来及其置县设郡考
梓潼由来及其置县设郡考
刘 文 蒲江林
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配合中央电视台拍摄和制作《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笔者对有关专家、学者、方志爱好者对梓潼的得名及其置县设郡历史质疑进行了考证,并以此文回应最近相关人士的垂询。
梓潼得名源于三种说法
老子《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恒名”。梓潼是文昌帝君悟道行善之所、弘文宣化之地,可谓“一贯道之”,而梓潼之名也堪称“恒名”。然而其名如何命名的呢?梓潼得名有三说:一是得名于梓潼部落国;二是得名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三是得名于梓潼县城所据的山水地貌。
第一种说法出自任乃强、杨立伟《四川地名考释•梓潼县考》,同时任乃强在其《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认为,梓潼是一个民族聚居区。族大人众,历史悠久。梓潼二字,“莽曰子同”。可以设想,二字是译民族本语的音,并无汉文意义。王莽将“梓潼”改作“子同”,并非他也提倡简化字,只是“译无定字”。使用“子同”二字,还有表明“同属子民”之意,亦即说明这个地区还有一部分民族未完全融合,仍自称为“子同”,即梓潼。笔者将此说法简称“任说”。而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 先秦部分》(1982年版)第11-12页可以看出梓潼属嘉陵江流域氐所在范围。
先秦梓潼为氐人所在范围
第二种说法出自明董斯张撰《广博物志》(卷四十),梓潼山原名尼陈山,为夏禹治水疏理河道陈放尼土的地方,故名。夏禹欲造独木舟,知尼陈山有梓木,径一丈二尺,令匠者伐之,梓树不伏,化为童子,禹责而伐之,先民以为尼陈山梓树为童子所化,故改尼陈山为梓潼山,又因驰水缠绕,以水为表,故名梓潼。这种说法简称“董说”。
第三种说法出自北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四)载,引《华阳国志》云,“以县东依梓林,西枕潼水,以此为名。”笔者简称其为“乐说”。而今梓林潼水之说已成为梓潼地方人士和一般学者流行之说。由于梓林潼水说成为流行之说,《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的地名记亦采用了此说。
究竟那种说法更准确呢?笔者认为,应该考证梓潼这一地名的历史。
据《梓潼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载:“梓潼之名传之久矣,远在夏商之际,即已有梓潼之名。”
再据西汉杨雄所著《蜀王本纪》载,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缘五女于蜀,蜀王中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由此文献可知,早在战国时期,“梓潼”已经载入古蜀史册。又据《西充县志》“充国县界,东连宕渠(今四川渠县),南接安汉(今四川南充),西倚涪县潺亭、梓潼,北邻阆中县。”西充是原充国的核心。这亦可傍证历史上可能存在梓潼国。而任乃强在其《巴蜀上古史新探》中则说:“梓潼还很早就建成了一座雷神庙,来显示它的民族威力。那就是今天还保存下来的七曲山的文昌庙。隋唐以后都说他是‘司禄命之神’,秦汉到南北朝都说他是凶恶的雷神。其庙叫善板神祠。这样以神道管理顽强的民族,可能是梓潼王创造出来的。”
另据最新的考古发现——里耶秦简第八层71简牍有这样的记载:“卅一年二月癸未朔丙戌,迁陵丞昌敢言之:迁□佐日备者,士五(伍)梓潼长辛見(亲)欣补,谒令□Ⅱ8—71二月丙戌水十一刻刻下八,守府快行尉曹。□8—71背。”这段话的大意为,秦始皇三十一年二月四日(即公元前216年二月四日),迁陵县丞昌如实报告记录如下:迁陵县佐即将任职到期,拟由来自梓潼县长辛見(亲)里老兵名欣的补缺,特别请示。时间为二月四日水十一刻刻下八(即约晚上十一点半),即由守府(洞庭郡府)快行(特快专递送达)尉曹(迁陵县司职卒徒转运工作的曹吏)。而湖南文物研究所编著的《里耶秦简》中的校注第一卷第54页指出:此事《二年律令• 律秩》(张家山汉简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93年)也有记载。同时里秦第八层1445简牍记载:“卅二年,启陵乡守夫当作,上造,居梓潼武昌,今徙为临沅司空啬夫”。这段文字是说,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梓潼县武昌里一个叫夫的人,从启陵乡守的职位调任临沅司空啬夫(即其主管官员)。2002年4月,发掘于湘西龙山县里耶镇的《里耶秦简》被学术界称之为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古的又一重大发现。《里耶秦简》记载了时间由秦始皇(含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前后约十五年秦王朝洞庭郡下辖的迁陵县档案。由此文物可知,里耶秦简两次提到“梓潼”,在秦代大一统时,“梓潼”已经载入秦帝国的历史中。
里耶秦简两次提到“梓潼”
据班固《前汉书》载:“五妇山,驰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 梓潼之驰水,流行于红土丘陵之谷壑间,蜿蜒回曲如蛇形,故先民呼为蛇水,又作九曲水。古蛇字写作虵,《汉志》书为驰,驰者,水流急也。故云,广汉郡有五妇山。今志亦有五妇岭的记载。而在汉以前没有潼水、潼江的称谓。郦道元《水经注》才将潼江称作梓潼水、潼水。《隋书》称潼江,沿用至今。因此,梓潼的最初得名是无潼水可枕的。
既然没有潼水可枕,那么有梓林可依么?《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载,袁还朴的旧志序中说,梓潼“求所为楩梓杞楠之材,无有也。求所为叔鲔王鳣之鳞,无有也。”袁还朴则系清乾隆年间梓潼县令,为清代《梓潼县志》首创者。
而在2000年,笔者还专门找《梓潼林业志》编纂者赵义才求证,梓潼是否在古时有梓林。赵先生经过多方考证,从气候和自然地理位置上看,梓潼有生长梓树的可能,也有梓树,梓潼人称之为“豇豆树”,但是否存在如董斯张撰《广博物志》中那种“百木之长”的木王,梓潼找不到上百年的梓树。只从仁和镇观龙场、原大新乡秋树村找到有云鳅树的线索。即或真有梓林,也不在今七曲山东部,而在县域东部。因此,从方志到现实,梓潼并不盛产梓木,可能“东依梓林”也不存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梓潼得名三种说法中,“任说”的推断——梓潼的由来是得名于,接近历史的真相,比较准确一些,“董说”“乐说”均缺少历史依据;而在《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采用“乐说”,则是千年来的约定俗成。
梓潼置县已逾2300年
郡县制保证了历史中国相对稳定和统一,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上的体现。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熊通;郡制起源于秦国,秦穆公嬴任好。其中中国历史上第一县叫权县,楚武王熊通(?~前690年)继位(前740年~前690年)三年后,挥师越过罗国,攻打并灭掉位于汉江平原西部的权国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将掠夺的土地分封给臣下,而是改权国为权县(治今湖北省当阳县东),设置县尹(以后称县令、县长),命斗缗(原权国国君)为权尹(可以世袭),把所有权力“悬”(其本意是“县”)挂在中央手中,加以管理,这是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被史学家称为“春秋第一县”。历史悠久的梓潼何时置县?也有三说。
一是西汉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所置。
二是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刘彻所置。
三是先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嬴稷所置。
笔者将这三种梓潼置县起始点简称汉高帝置说、汉武帝置说、先秦昭襄王置说。在《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我们采用了先秦昭襄王置说。
汉高帝置说的主要依据为,梓潼县现在最早县志朱帘所修《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载:“汉,梓潼县,寻为广汉郡治。”而广汉郡为刘邦在公元前201年分巴析蜀所置,其意为“广大汉业”,梓潼县为郡治所在地。清张香海所修《梓潼县志(咸丰八年版)》沿袭了《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直隶绵州志》(乾隆版)卷一记载:“汉置梓潼县,寻为广汉郡治。”《四川通志》(嘉庆版)卷二记载:“汉置梓潼县,为广汉郡治。后汉移郡治县雒县。”《华阳国志•蜀志》(《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三记载:“广汉郡,高帝六年置,属县八……南支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汶山,北接梓潼,东接巴郡。”
汉武帝置说的依据是,《寰宇记》引《华阳国志》云:“汉武元鼎元年置。以县东倚梓林、西枕潼水,以此为名”。而据曾校订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常璩所著《华阳国志》的任乃强先生考证:“今按:此谬说也。常璩未有此文。《前汉志》: ‘广汉郡,高帝置’。以梓潼县为郡治。”
先秦昭襄王置说的依据是,《梓潼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则明确说:“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始于蜀地实行郡县制,置蜀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梓潼始置县,隶于蜀郡。”《梓潼县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则沿袭前志说法:“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年),秦王朝开始在蜀地实行郡县制,置蜀郡,划蜀地为三十一县,梓潼县始置,隶属秦国蜀郡。”
绵阳师范学院蒋志教授所著《绵阳简史新编》(绵阳社科丛书之十三 绵文广新内2016第202号)载:“公元前285年,以原蜀国地设蜀郡,蜀郡下辖19县,绵阳市境内为蜀国辖地,设有郪县(辖今三台、盐亭、射洪、中江、蓬溪一带)、梓潼县(辖今梓潼、游仙、涪城、安州区和江油的一部分),这两个县在蜀国时都是古老的部落发展而来的小国,原部族的力量还较强大,因而在此设县,加强统治。”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在湖北张家山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竹“简四四七”编号中有“临邛、新都、武阳、梓(湩)[潼]、涪、南郑…(共52县)”竹简中“秩”字,是指古代官吏的俸禄之意,“官人益秩,庶人益禄” 。从竹简释文中看:吕后二年,即高后(吕雉)二年(前186年),距秦朝灭亡仅16年,梓潼县已经在汉朝庭的典籍上。因此,梓潼更不是汉武帝刘彻元鼎元年始置。
里耶秦简简牍8-71编号“梓潼长辛見(亲)欣补”、简牍1445编号“卅二年啓陵鄉守夫當坐上造居梓潼武昌今徙(正面)” 等有“梓潼”的记录。《里耶秦简》校注第一卷第54页对“梓潼”的注释为:“梓潼,县名。《汉书·地理志》 属广汉郡,治所在今梓潼县。”由此可以推断,梓潼在秦帝国时已经置县。
按《汉书·高帝纪第一上》记载,鸿门宴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后的二月,即乙未年(前206年),“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背约,更立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之,都南郑(今汉中市)。”“巴、蜀、汉中” 三郡所辖41县为秦朝沿袭秦国在巴蜀实行郡县制雏形的延续。按原县志办主编敬永金老先生的指导,笔者查找到,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谭其骧主编, 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代郡县列表·蜀郡》“可考县名”栏内,巴、蜀、汉中三郡共置“四十一县”的县数中,梓潼县为蜀郡十八县之一。由此完全肯定,梓潼至迟在秦代已经置县,而非汉初刘邦始置。
再据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5年10月版)战国时期全图梓潼县在蜀占据明显位置。这也说明梓潼是秦代以前设置的古县。又据《中国史话》丛书之《梓潼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封底阅读提示框提要第一句明确说:“梓潼历史悠久,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置县。”而其上“中国史话”徽标标注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史话》丛书由编委会主任由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担任,而副主任则有时任分管中国地方志工作的社会科院副院长武寅,中国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专家为副主任或委员。《中国史话》丛书之《梓潼史话》出版发行时正是梓潼置县2300年之时。梓潼置县至今,县名一直沿用,仅王莽篡汉时,一度(9年至25年)改名子同;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至隋大业三年(607年)期间,曾易名安寿,前后共计70年。此外,虽迁移并析不定,但县名再无变更。
梓潼曾五度为郡治
今日之梓潼仅是1443.92平方千米的小县,时百姓戏称“寡梓潼”,而清代康熙二十五年时任知县袁还朴称之为“小邑”。历史上的梓潼却是大县。任乃强先生在《巴蜀上古史初探》中说:“可以设想,古梓潼县地面很宽,约有今天梓潼县的十倍。大概东抵嘉陵江,西至成都平原,包括有今天梓潼、剑阁、青川三县和江油、绵阳、盐亭和广元的大部分。”任乃强先生这种说法从《二年律令·秩律》竹“简四四七”编号(中有“临邛、新都、武阳、梓(湩)[潼]、涪、南郑…”)可以得到印证。梓潼在汉初列第四位。
另据2019年3月梓潼籍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副教授李春林向笔者传过来的“梓潼令印”图片,据笔者考证,这枚收藏收上海博物馆的“梓潼令印”系东汉时期梓潼行政首长的官印。在秦汉时期,大县行政首长为“令”,小县行政长官则是“长”(西汉县区的户数,《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蒋志教授所著《绵阳简史新编》亦说,始置的梓潼县是原梓潼部落国的辖地。
东汉“梓潼令印”
梓潼在历史上曾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两汉时有相当高的美誉度,据重庆三峡博物馆国宝级文物景云碑记载,广汉郡梓潼县人景云曾在东汉永元年间在朐忍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任县令,终于任上,碑文赞景云“君其始仕,天资明括,典牧二城,朱紫有别,强不凌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蒸民乃厉,州郡并表,当享符艾。大命颠覆,中年殂殁。如丧考妣,三载泣怛,追勿八音,百姓流泪。魂灵既载,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吏民怀慕,户有祠祭,烟火相望,四时不绝。”
景云碑
梓潼“地联秦关,路当扼蜀”,北扼剑门,南控涪江,号称“扼控三巴,益州衿领”,是古蜀国北部门户,其南部系石牛道险夷交接点(五妇岭送险亭即是古蜀道显著路标),为“千里栈道,通于蜀汉”的南栈出入口,有“蜀北锁钥”之称,成为“商旅云集、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自汉初至南北朝西魏,前后750余年,梓潼多为郡守治所。
2018年9月29日,四川省地情网转载梓潼县方志办颜友所撰《梓潼:县名沿用两千多年,五度为郡治》,其文中说:“梓潼曾经五度为郡治所。一是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分巴郡、割蜀郡之地,在梓潼设广汉郡,史称‘分巴割蜀以置广汉’。下辖梓潼、什邡、涪、绵竹、葭萌、郪、新都、白水、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等13县道。二是初始元年(9年)王莽篡汉,为避‘汉’字,将广汉郡改名子同郡。东汉建武元年(25年),公孙述据蜀,建‘大成国’,将子同郡改名就都郡,梓潼县仍置,为就都郡治地。三是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分广汉郡之地,在梓潼置梓潼郡,分辖梓潼、剑阁、汉德、涪县、汉寿、昭欢、白水等县。四是梁天监四年(505年),北魏尚书刑峦入蜀,夺得南梁之梁、益二州十四郡之地,在梓潼设梓潼郡,隶属东益州。五是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大将军尉迟回伐蜀,在梓潼置潼州郡(又名潼川郡、东川郡),隶属益州大都督始州。”
据《绵阳市志》(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上卷《广汉郡治考》记载,梓潼县作为广汉郡治长达316年。2012年12月中旬,梓潼县城两路口出土文物证实了广汉郡治设于梓潼神乡的文献记载,也证实了《汉书•地理志》郡治梓潼“有工官”的说法。2015年1月,梓潼县城九旬老人仇子元还对笔者说,解放前,在今梓潼县城老区文昌路还有“古潼川郡”木坊,其大致位置在原县政协地段,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县城北门,过门就为北门外。
结论:
梓潼得名由来悠久,可溯至先秦以前,其名源于“梓潼(民族部落)国”的称谓;梓潼始置县于公元前285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设置郡县制早64年;梓潼曾五度为郡治,首为广汉郡治,终为潼川郡治。
作者简介
刘文,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员,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梓潼县委党史研究室兼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副主任。
蒲江林,绵阳市地方史志学会常务理事,梓潼县委党史研究室兼县地方志编纂中心主任。
古典戏剧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遗产,难以与戏剧这个概念本身区别
\r\r\r\r\r 罗马的遗产\r \r\r\r\r 第九章 戏剧\r\r戈登·布
\r\r古典戏剧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遗产,难以与戏剧这个概念本身区别开来。博吉西曾经写过一个著名的寓言,来说明阿威罗伊面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所产生的困惑(《阿威罗伊的探索》,载唐纳·A.耶茨与詹姆士·E.埃尔比主编:《迷宫》,纽约,1964)。他的结论是:悲剧是颂词,而喜剧是讽刺诗或者诅咒(“《古兰经》和圣地的摩哈拉加斯[mohalacas](1)中充满了令人敬佩的悲剧和喜剧”)。如果不考虑后来的戏剧传统,让人们了解戏剧究竟是个什么概念,这可能是一个受过教育和聪明的人从中世纪伊斯兰教文献中能够得出的最好的结论。虽然那个伟大的阿拉伯哲学家终生都在研究亚里士多德,但现代最麻木的电视迷也许比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都更加全面。在新的《希腊的遗产》中,T. G.罗森迈耶开篇即援引博吉西的话强调说:“这个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戏剧艺术并不是一个世界现象,不是所有文化都与生俱来的。”罗森迈耶进一步证明,那如今仍然让我们着迷的戏剧传统,乃是独特的西方事物,和其他任何文化都不同。从长远的观点看,近代的戏剧革命并不是如阿陶德–诺的戏剧或者巴林舞蹈坚决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是接受东方影响的结果,而是回归到西方戏剧起源时的形式。虽然我们知道,自从埃斯库罗斯和古代希腊的戏剧节日以来,西方的戏剧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可是,如果仅有外来的影响,而没有足以支撑的共同的起源,我们肯定很难想象,西方会产生出像贝克特的《决战》那样经典的先锋派戏剧。
\r\r关于罗马的戏剧,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希腊文献的拉丁化是它们能够经历古典文明崩溃后的动荡而幸存下来的主要方法。关于它们的存在,我们有时只有很稀少的线索。很可能的是,塞涅卡在创作其悲剧时,目的就是供人们朗诵,甚至是个人阅读,而不是供在剧场中表演的。到中世纪时,无论是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都已经不知道如何利用普劳图斯和太伦斯等戏剧技巧大师的剧本了。许多人认为,它们是用对话体精心创作的叙事诗。这个理解不比阿威罗伊准确多少。可是,人们还是可以再度发现戏剧的舞台背景的。西欧戏剧的繁荣,又是和拉丁语文献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确实,西欧对希腊先驱者真正感兴趣,一般来说还要等到几百年以后。那时,作为有着自己独特历史和传统的国际性艺术,戏剧已经有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直到1715年,才有人想到要出版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英译本。就西方戏剧的发展来说,罗马是一个关键的连接点,当我们说到希腊戏剧影响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在某些时候或许更加准确,也同样是它们的罗马后裔的影响。
\r\r可是,从它们是希腊的后裔,从它们的基因有明显的希腊特色来说,有关古典戏剧影响的绝大部分内容应当属于另一部著作,而不是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拉丁语文学文化有意识的保守,才使罗马能够成为希腊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桥梁。在这个领域,就像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罗马作家努力去做的,乃是明显的模仿。普劳图斯和太伦斯常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他们剧本的基础是哪一个或者哪几个希腊的剧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逐字直译”(verbum de verbo expressum)。所以,根据这些理由,在这个传统的范围内对他们进行评价,是有某些道理的。18世纪以来,人们的目光普遍从罗马的戏剧转向雅典的戏剧,因为人们认为,罗马剧本能够提供的东西,我们不仅都可以在希腊的戏剧中找到,而且希腊的戏剧更加持久、更加多样和有趣。20世纪对罗马戏剧的尊重,虽然已经让人们知道,事情并不止于此,但也没有能够真正突破上述结论。所以,在接下来的评价中,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在罗马戏剧中存在而在希腊戏剧中缺乏的内容,也就是说,罗马人对戏剧发展的独特贡献。而正是罗马人,才使得戏剧的延续成为可能。这个任务比希腊戏剧给我们提出的任务要轻些,但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困难。
\r\r对喜剧来说,我们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且可能也是无的放矢。我们所了解的绝大多数希腊喜剧当然是旧喜剧,阿里斯托芬的剧本是其代表。可是,这种形式从来没有能够成功地移植到任何其他文化中去。另一方面,继承旧喜剧的新喜剧,虽然在古代世界广受欢迎,并且影响巨大,其历史却几乎完全是破碎的;在本世纪米南德的《吝啬鬼》发现之前,没有任何新喜剧的剧本完整地保留至今。我们关于新喜剧的知识,绝大部分是从罗马人的模仿之作中推测或者引申出来的,例如,我们对波斯狄普斯《相似的人》(除了标题外,该剧什么都没有流传下来)的情节的了解,就完全是猜测,猜测的基础是普劳图斯的剧本《孪生兄弟》。这些资料填补了新喜剧历史中的部分空白,但不可能使我们获得准确的知识,让我们足以判断它与普劳图斯以及太伦斯的剧本之间有多少相似,又有多少不同。虽然耐心的学术研究至少已经能从中分离出某些罗马人的创新,借用爱德华·弗朗克尔的话说,是从普劳图斯的戏剧中抽出普劳图斯因素,然而,仍然有某些东西限制了我们对新喜剧发挥作用方式的了解。由于新喜剧与社会底层的生活联系密切,使用的是街头俚语,因此总是带有其社会和历史环境的色彩,有其特定的节奏与舒适感。如果我们说一个有同样情节、同样是希腊名字的希腊与罗马的喜剧,分别受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欢迎,几乎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但也几乎什么都没有说。普劳图斯,特别是太伦斯的影响确实巨大,但对后世的模仿者来说,他们的“罗马特色”可能是其最微弱的部分,因为这些模仿者很容易地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的玩世不恭,或者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新教徒的虔诚,取代了原作的特色。
\r\r如果我们想在罗马戏剧对后世的影响中找到罗马因素的话,那得从悲剧中寻找,因为它的背景长期以来一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相对抽象。对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大多数悲剧作家来说,悲剧的世界实际上就是古典的罗马。当他们将背景确定在那时时,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遵从了塞涅卡悲剧作品的指导。在塞涅卡的这些作品中,包括《屋大维娅》(并非塞涅卡之作,而是托名)。除了那些更具神话色彩的悲剧外,《屋大维娅》中的坏蛋是尼禄,塞涅卡本人也成了其中的一个人物,因此能够让人们确定这些悲剧的背景。对专制主义盛行的欧洲来说,这些以罗马帝国为潜在背景的悲剧,肯定比希腊传统中出现的、更加分散和模糊的背景更适合需要。由于共同的兴趣,剧作家们利用塞涅卡戏剧技巧的某些特征(这些技巧把塞涅卡的剧作与希腊先驱者们区别开来),并且把它们变成了戏剧艺术宝库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部分,熟悉得竟让我们分辨不出它们是来自罗马人的遗产。在谢尔盖·埃森斯坦因的电影《伊凡雷帝》第2部中,当伊凡向波雅尔贵族们宣布,他将决心击败他们的阴谋时,他说的是,他将按照他得到的名声,即电影赋予他的称号行事,“我将是‘恐怖的’”(2)。这种固执己见的话语,可以一直追溯到塞涅卡可怕的女主人公美狄亚那里,这中间经过文艺复兴时代戏剧艺术的改造,如“我将总是俄狄浦斯”(io saro sempre Edippo,路多维科·多尔策:《伊奥卡斯特》,第5幕),或者“我将是克娄巴特拉”(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第3幕,第13场第186行)。塞涅卡在《美狄亚》中是这样写的:
\r\r奶妈:美狄亚……\r 美狄亚:我厌恶逃避。\r 奶妈:美狄亚……\r 美狄亚:我将成为我自己。
\r\r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包括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和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都不曾用下面的方式来想象他们自己:以为他们的名声已经提前存在,并用同样的口气来谈论自己。可是,如今我们却认为这样的修辞手法和心理描写太正常了,而正常本身就说明,我们和塞涅卡非希腊的极端戏剧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由于埃森斯坦因受到斯大林所树立的榜样的困扰,而且对他的保护存在矛盾心理,因此,他的电影利用近乎怪诞的历史面纱,把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同样也出现在帝国时代一个最富有尼禄特色的人物等同了起来。他运用塞涅卡的戏剧修辞手法,来表现伊凡难以遏制的、野心勃勃的自我。
\r\r然而,如果不把悲剧和喜剧的命运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将无法说清戏剧遗产的经历。喜剧的生命力相当顽强。与埃森斯坦因的电影可以对抗的,是最近迪斯尼公司推出的一部名叫《大事》的电影(1989年出品)。它的推出再次证明,《孪生兄弟》保持了几千年的活力依然不衰(它事实上表明,相貌相同的孪生子的花样,只有借助于电影镜头的帮助才能真正实现)。不过,从古典古代以来,罗马化的新喜剧一直比塞涅卡的那些悲剧得到更广泛的使用,而且就其与戏剧实验和发现的关系来说,它与戏剧的主流也更加接近。尤其是太伦斯的那些喜剧,从没有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完全引退。在中世纪,喜剧(comedia)逐渐失去了它类的特殊性,具有了这样一种含义:它可以用在那些具有太伦斯情节的诗歌型寓言,或者关于灵魂升天的叙事身上(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诗人维吉尔曾把自己的主要作品称为“悲剧”[tragedia])。虽然但丁引用过太伦斯和塞涅卡的作品,但仍明确地把喜剧定义为“叙事诗歌的一种类型”(见罗伯特· S.哈勒编辑和翻译的《但丁的文学批评》,林肯,内布拉斯加,1973年版,第100页)。可是,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潮流再度逆转,最后,这个词在不止一种方言中变成了“戏剧”的同义词,而“喜剧作家”变成了“演员”的同义词。像“法兰西剧院”(the Comedie-Française)一样,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r\r即使在中世纪,古典的榜样也能激励人们创作出戏剧类作品。10世纪撒克逊一个名叫霍斯维萨的甘德尔海姆的修女以太伦斯为样板,创作出一系列圣徒的传记,其戏剧体的语言说明,它们可能是为表演创作的。她机敏地把年轻人的爱情追求转变成对殉教烈士们纯洁情感的追求。14世纪,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人们一个主要的目标是把罗马的喜剧转变成现代戏剧。从长远的观点看,它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许多相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彼特拉克本人至少就有意模仿太伦斯写过一个剧本,其题目叫《语文学》,足以说明问题,可惜只有一行格言流传到今天。据说他毁掉了所有他认为不如原作的作品。对罗马戏剧的发掘和转化工作,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仍在继续,科萨的尼古拉于1428年发现的普劳图斯的12个新剧本,给有关的努力以新的推动。15世纪后期,普劳图斯和太伦斯的一些戏剧在几个地方都被搬上了舞台,此外,一些杰出的作家如阿尔贝蒂、布鲁尼、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皮科罗米尼(未来的教皇庇护二世)等人,也创作了一系列新拉丁派剧本。提图·李维奥·德弗鲁洛维希(1432—1438)的七个剧本,本身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oeuvre)。这些作品为16世纪用方言创作的博学派戏剧(commedia erudita)提供了学术背景。博学派戏剧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在戏剧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并且让该世纪一些著名文化人如阿里奥斯托、阿伦提诺、马基雅弗利、布鲁诺等人在这个领域中花费了不少精力。马基雅弗利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可以理解的是,最初,他试图从一个已经失传的、名为《假面舞会》(le maschere)的剧本中恢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在放弃了该项工作后,他翻译了太伦斯的《安德罗斯的姑娘》,《安德罗斯的姑娘》成为他创作《曼托罗华》的准备,而该剧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戏剧所取得的最富有独创性的成就。
\r\r总体看来,上述作品在传统和创新之间扮演了联系人的角色,几乎可以说是人们模仿古典过程中出现的典型表现。罗马喜剧的某些形式特征如五幕剧、长篇大论式的开场白、场景选在相邻房屋前开阔的街道上以及结尾时对观众欢呼的期待等,至此变成了通例;喜剧的核心部分,如诺特诺普·弗里所形容的,是跨历史的,“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一个年轻的男人追求一个年轻的女性,可是他的追求遭遇到某些人的反对。反对通常来自父母方面。临近结束时,情节上会出现某些转折,从而使男主角实现其愿望。”(见《解剖批评》,纽约,1966年,第163页)或者借用太伦斯本人更加活泛的定义,他的规则是:
\r\r逃亡的奴隶、\r 善良的姑娘、心怀恶意的、小孩的\r 把戏、仆人对主人一连串的欺骗、\r 爱情……仇恨……还有嫉妒……接二连三出现,\r 凡是能用上的,全部用上。
\r\r(《阉奴》,第36—41行)
\r\r对意大利的喜剧来说,上述规则显然也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业规范。可是,当形式成熟后,它也开始大量吸收新时代的生活素材,从而创作出新的喜剧和讽刺性人物(例如,阿里奥斯托的《魔术师》具有非常明显的反教会倾向。所以,教皇利奥十世于1520年取消了该剧原定在梵蒂冈的演出)。同时,戏剧中出现了一个明显不同的新领域,在这个新领域中,年轻人的爱情被驱逐出去了。霍斯维萨曾经把罗马喜剧改造成适合修道院性理想的圣徒传,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则让它们适应新的伦理道德的需要。在他们的剧本中,皮条客和所占的突出地位,并不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爱情中还有相当混乱的性关系,并且最后常常把它变成合法的婚姻。不管是在普劳图斯和太伦斯的喜剧中,还是在任何其他的罗马文献中,都不曾有下面的演说中所包含的东西。在《波利森纳》(据说为布鲁尼所作)一剧中,与剧本同名的女主人公支持女性的性自由。同样,在古典喜剧甚至在太伦斯让人震惊的剧本中,也不曾出现在几个意大利剧本中出现的那种坦白的、犬儒式的性安排。在乌格利诺·皮萨尼的《菲诺格尼娅》(1430—1435)中,与剧本同名的女主人公发现,她的情人竟然使她先后与他的朋友们有了性关系,而这竟然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掩盖他第一个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她最后嫁给了一个农民,目的是让他当一个无知的乌龟。确实,文艺复兴时代最突出的变革是,通奸成了人们所期待的喜剧的题材,而血缘上的敌人和嘲弄的对象,由父亲变成了丈夫。马基雅弗利在《曼托罗华》的结尾处,让他的男主人公耍了一个诡计,以便年老的丈夫默许他年轻而一直纯洁的妻子与人通奸,并把手伸到床单下,以弄清正在发生的事情。马基雅弗利利用比喻的手法,把老人的妻子命名为卢克里齐娅,以表现自古典古代以来女性性理想变化的程度。
\r\r这里出现的真正的常量也许是欺骗,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路多维科·卡斯特维特罗认为,它是该类戏剧的基本特征(《卡斯特维特罗论诗艺》,安德鲁·邦吉奥诺译,宾汉姆顿,纽约,1984年,第213—217页)。爱情也许会改变它的色彩,但该类戏剧真正的关注点并无变化。那些奇妙的而且常常非常复杂的情节,都围绕爱神展开,从而编织出一张由错误的目标以及误认的人物构成的场景。他们的行动和相互关系必须相当复杂,以使情节有趣,但又必须相对清楚,以便人们可以把握。新喜剧及其同类真正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更多的是它的公开调情,而不是剧中任何人物提到的性行为或者其玩笑的性质。太伦斯突出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特别精于此道。据说他的特长就在于能把简单的诡计变成双重的阴谋(《自责者》,第1—6行)。古典先驱对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那些即将成为剧作家的人有吸引力的地方,更多的也是这个方面,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曼托罗华》中就包含一小段明显含有味的、歌颂阴谋[inganno]的颂词)。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从罗马人不同的剧本中把各种情节汇集起来,压缩成一个新的情节。作家们自己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想像》(I suppositi,1509年)一剧的开头,阿里奥斯托就声明,剧本中的阴谋是把普劳图斯的《俘虏》和太伦斯的《阉奴》中出现过的阴谋进行新综合的结果(声明本身出自《安德罗斯的姑娘》的开场白,意大利语剧本的名字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双关语,涵盖了喜剧中所有的抄袭现象)。如果一个作家从他人那里借鉴了某一特殊的情节,并对之进行高雅、复杂的改造和转变,那么,他就成了这个传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例如,大主教比别纳所以能在戏剧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因为他在《卡兰德里亚》(1513年)一剧中,既有模仿也有超越《孪生兄弟》之处。他把原来的孪生兄弟改造成了兄妹关系,他们之间的可转换性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我真不明白,可是利狄奥已经从一个男人变成了女人。当我抚摸他时,我发现了这个事实。虽然我被剥夺了乐趣,但我既为我自己也为利狄奥悲哀,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最为自豪的东西。”引自埃里克·本特利编:《意大利的戏剧天才》,纽约,1964年)。这个设想最后确实给文艺复兴时代的戏剧以重大影响,创造了一个亚种——性伪装喜剧。
\r\r情节上的这种复杂性,有时是命运操纵的结果,但至少部分归因于人物本身有意识的行动。主要的阴谋家也许是恋人中的一个,但常常是一个狡猾的朋友或者仆人。除了实际的动机外,他们还对玩弄此类阴谋感到特别高兴(有人曾经提出,这类喜剧的前提之一是:一个人物对行为控制的程度和他卷入行动的程度成反比。见帕尔麦·波维编:《太伦斯喜剧全集》,新不伦瑞克,新泽西,1974年,第230页)。然后,舞台上的骗子会在幕后遇到威严的作家派到现场的代表。当整个文化都在忙于重新学习讲故事的戏剧化方式时,这种类比就获得了特殊的力量。在新的和其他叙事传统中,相对完善的情节是存在的,但要在舞台上把它们表现出来,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中世纪晚期的宗教和民间戏剧所提供的指导少得可怜。在文艺复兴戏剧史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古典先驱的模仿也许是学习此道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模仿已经“改变了欧洲戏剧所有的形式”(利奥·萨林加:《莎士比亚和喜剧传统》,剑桥,1974年,第187页)。
\r\r如其属名所示,博学派的喜剧,由于常与模拟古典作品联系在一起,其文学影响确实受到某些限制。在其本土,它未能导致受欢迎的民族戏剧的兴起。而16世纪末的欧洲其他国家,都出现了民族戏剧。它的演出场地仍然在贵族的宫廷和人文主义者的小圈子里,其表演者绝大部分也是那些对文化声望而不是戏剧职业更感兴趣的业余人士。可是,这些限制要比通常出现的此类障碍更容易克服。无论是单个的剧本,还是它们所树立的样板,都曾经在其他地区的公共剧场中上演,而且常在十分关键的时候上演。乔治·查普曼有影响的早期喜剧中,有一个是亚历桑德罗·皮科罗米尼的《亚历桑德罗》的改写本,它的英文名称《五朔节》表明了这一点。另一个叫《愚人》的剧本,来自太伦斯《自责者》的意大利语改编本,只是在剧本中增加了一个人物,他说话更像剧作家本人,而不是文艺复兴时代舞台上的任何其他人物:
\r\r你由我管制,\r 你将会看到,我会把这个\r 粗糙的情节改造得多么完美,\r 盲目的机遇带来的\r 仍是盲目的意见和建议。
\r\r《想象》被乔治·加斯科因翻译成《以为》,莎士比亚又接过了它,把它改成了《驯悍记》中鲁森修和比恩卡的故事,并且和另外一个情节结合了起来。在更早时期的练习剧本《错误的喜剧》中,故事的核心来自《孪生兄弟》的双重计谋。比别纳对这个主题的改造通过佚名的《被欺骗的人》(1531年;人们很恰当地认为,卡斯特维特罗是最可能的作者人选)实现的,它为《第十二夜》提供了主要情节,而且是莎士比亚成熟的喜剧中最重要的一个噱头。
\r\r即使在意大利,博学派的喜剧也产生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它促使安格罗·贝奥科创作出农民喜剧。此人以舞台艺名伊尔·罗赞特知名,坚决反对16世纪早期意大利戏剧界某些势利的倾向,特别是它对托斯坎纳文学语言的推崇以及远离农村下层的倾向。贝奥科特别了解农民,他早期的剧本几乎都是布莱希特式的小品文,使用的是帕多瓦方言,具有基本的幽默感,相对说来,比那些表现城市同类题材的戏剧更加喧闹和粗鲁,性关系上也更加混乱。可是,贝奥科晚年的作品努力适应古典喜剧的规范和情节线索,《雨》和《空缺》(1533年上演)两剧很快就能让人看出,它们模仿的是普劳图斯的《绳子》(rudens)和《赶驴》(asinaria)。贝奥科的作品所展示的,与其说是博学派喜剧传统的局限性,不如说是它不可穷尽的适应性。
\r\r然而,最能表现博学派喜剧影响的,是16世纪中期意大利戏剧职业化的最后完成以及随之而来的“commedia dell’arte”的发展。Commedia dell’arte这个词在英语中最好的翻译可能是“戏剧协会”。在它的名下集中了一批公司,随着他们在欧洲大陆上的巡回演出,他们原本地区性的能力,现在随着他们令人惊奇的、都市化的样板,发散到各地,从而成为以后两个世纪中给欧洲戏剧以巨大和直接影响的主要渠道(莫里哀的公司多年里和他们一起住在巴黎的波格涅旅馆)。由于影响的直接性,我们很难准确计算他们影响的程度。公司在身后都没有留下文献,有关的记载也很少。他们的基本模式是:依靠关键演员和框架似的场景进行集体临时创作,所有准备工作都服从表演时的需要,效率就是一切。
\r\r在某些用法里,艺术(dell’arte)和博学(erudita)是一对反义词,两种传统之间的对比也相当明显。然而,它们之间的鸿沟更多的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民间戏剧和人文主义有共同的来源。弗拉米尼奥·斯卡拉出版过《戏剧集》(1611年出版,亨利·F.萨勒诺把它翻译成《戏剧剧本集》,纽约,1967)。他把作者和古典古代一些伟大的作家并列对待,并提到,他希望通过“印刷纪念他本人和其作品”的方式,取得可与古代作家比肩的不朽名声。斯卡拉及其余作者的戏剧集清楚地表明,协会主要作品的主线还是新喜剧:年轻人的爱情,老人的干涉,最主要的,还是阿里奥斯托称为“假想”的误认以及有意的欺骗。此外,新喜剧作家的创新能力,主要体现为各种可能性的更加完善和精巧,孪生子依然是最受青睐的题材。斯卡拉的剧本中有几个涉及孪生子,其中一对是哥哥和妹妹,其他人的剧本中也有孪生子,甚至出现三胞胎。可能的情况是:莎士比亚和其他作家或者通过阅读拉丁语及意大利语作品,或者通过观看与道听途说,从这些资料中得到灵感,继承了这些题材。剧本中经常出现的某些人物与古典喜剧中的人物相当接近:潘塔罗涅是老人,奥扎齐诺是坚定的恋人,卡皮塔诺·斯帕文托是吹牛的士兵。另一些人物则变化明显。狡猾的奴隶,因为与民间传说混合,在一系列新作中大量出现,他们的名字有阿列齐诺、普尔希列纳、布瑞格拉等。戏剧协会并不逃避博学传统,而是愉快地把它与其他喜剧的可能情节融合起来,把它变成爵士喜剧的材料。
\r\r罗马喜剧影响的不同方向,本身就是它相互补充特点的曲折反映:形式上的灵巧和内容上无可遏止的活力。实际上,也就是罗马喜剧的太伦斯特色和普劳图斯特色。一条线是要人们灵巧地编出好剧本,另一条线是把欧洲职业表演与小丑表演结合起来。当两者的融合达到某种平衡的时候,就产生出那种广义上可以称为近代古典喜剧的作品,它们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莫里哀。此人既读过拉丁语文献,也与意大利人一起表演过。近代古典喜剧产生后,罗马喜剧仍在欧洲戏剧史上经常以新的面貌出现:康格里夫和狄德罗都把太伦斯欢呼为他们的导师,吉拉都有意识地把自己最著名的剧本称之为普劳图斯《安菲特里翁》的第38种版本(更早的时候莫里哀也这样做过)。但是,古典戏剧作家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在16到17世纪完成,并且和他们具有的生命力以及能量一道,被吸收到各国方言戏剧中了。
\r\r罗马悲剧的命运在某些方面与罗马喜剧相同。尽管悲剧看起来享有更多的尊重,但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人们就把两者视为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事物。复兴古典喜剧的计划,不可能和复兴它更高贵的孪生兄妹分割开来。第一部“近代”悲剧的出现,实际上比彼特拉克的《菲劳劳吉亚》还要早。1314年,阿尔贝提诺·莫萨托在帕多瓦用拉丁语写出了《爱色里尼斯》。它本身又受到伊达拉里亚抄本重新面世的影响。在重要的伊达拉里亚抄本中,有塞涅卡的悲剧集。同时,它还受到罗瓦托·德·罗瓦提“原始人文主义者”学术成果的影响。正是在他们那里,塞涅卡悲剧的韵律自古代以来首次得到可能正确的理解。这部新作帮助作者在次年赢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授予这一称号,乃是公民们对莫萨托的感谢,因为他清楚地指出了塞涅卡的悲剧和他本人所处时代之间的联系。《爱色里尼斯》的主题不是神话,而几乎是当代的事件。他描绘的是爱泽林诺·达·罗马诺谋杀犯似的一生。此人在13世纪曾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贵族,威胁着帕多瓦。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他为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残忍的新风格的先驱。莫萨托在剧本中把他比作尼禄,塞涅卡本人以这个疯狂的皇帝为原型,描绘出一帮恶棍的形象。基于共同兴趣所产生的联系在意大利以外和14世纪以后继续保持,从而确保了塞涅卡悲剧的突出地位。即使在希腊悲剧为人们所知的时候,塞涅卡仍维持着自己的影响。
\r\r可是,这种联系也使那些即将成为悲剧作家的人接受了塞涅卡相对静止的戏剧技巧。后来,人们把他们与其雅典先驱者进行了不够公平的比较,认为“塞涅卡剧本人物的行动……就像一帮坐成半圆形的歌手一样,每个人都轮流完成他的‘任务’,或者像在一场闲聊、演唱中一样,背诵歌词和台词。如果是希腊的观众的话,我怀疑他们能否坚持听完《疯狂的赫克勒斯》的前300行”(T. S.艾略特:《论文选》,纽约,1950年,第54—55页)。这类批评不免有缺乏想象力的危险。在20世纪的戏剧中,塞涅卡所以受到特别注意,正是因为他戏剧技巧的严肃性。彼得·布鲁克赞扬他“把戏剧从场景、服装、舞台动作、姿势和事实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他所肯定的,正是艾略特讽刺的,“剧本所要求的,不过是一帮像树桩一样戳在那里的演员”(艾略特:《塞涅卡的〈俄狄浦斯〉导论》,特德·胡斯改写,纽约花园城,1972年,第5页)。可是,要把这种伯克特式的停顿作为戏剧冲突来感受,我们必须把它与通行的、更加常规的戏剧框架进行比较。较常规的戏剧给人们的期望在塞涅卡时代仍然存在,但只是在人文主义者重新接受以后,才得到恢复。对人文主义者来说,塞涅卡的文本既有阻碍,又有推动作用。《爱色里尼斯》中韵文体的舞台指导表明,尽管作者来自新的学术背景,但他显然是在中世纪错误的戏剧观念影响下从事创作的。作品第一次成功的演出可能只是一个演说家在那里朗读。虽然后来的创作者摆脱了这种混乱,但模拟的悲剧在很长时间里仍然是由朗读而非戏剧表演动作支配的。在这方面,悲剧一直落后于喜剧。
\r\r总体上看,人文主义悲剧传统比喜剧更加薄弱。16世纪以前,用拉丁语写作的悲剧不到六部,而且没有一部出自特别著名的作家之手(第一部是例外)。在16世纪的意大利舞台上,与博学派喜剧并存的有一系列悲剧,不过数量要少,而且作者的名气也不大。他们是:坚巴斯提塔·吉拉狄·欣提奥、路德维科·多尔策、路易吉·格罗托。他们的圈子也仅限于在那些上层观众面前进行文雅的试验。他们最显著的国际影响来自他们对塞涅卡邪恶竞赛的系统发展,从而把恐怖和愤怒的逐步升级变成了人们对悲剧的主要期望。他们在英语中的同行是《提图斯·安德罗尼科斯》(你对我的女儿比菲罗美尔更糟,我所得到的报应也比普罗格涅更惨)。它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孤独也说明了这一点。
\r\r16世纪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发现,以及卡斯特维特罗对行动、地点和时间三一律的相关总结,刺激了另一类人文主义悲剧的兴起,它更加关注形式的严格而不是内容的可怕。法国悲剧作家罗伯特·加尼尔和安东尼·德·蒙克莱田在该领域取得的专业上的成功(succes d’estime),在其他国家产生了大量模仿者,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的比德福德女伯爵和她的小圈子,他们中有萨缪尔·丹尼尔、福克·格里维尔,甚至包括托马斯·库德。16世纪90年代,他们出版了女伯爵的原作和译本。女伯爵的兄弟腓力普·锡德尼在《为诗歌辩护》中,支持过这种“常规的”悲剧。在当时,这并非不正常的呼吁,特别是在那些杂乱的民间戏剧已经开始扎根的国家中。可是,虽然他们非常诚恳,但这些剧本仍不无道理地变成了主要的标志。这些标志既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偏见给戏剧带来的危险,也显示了仅从文学角度去研究舞台的愚蠢。由于难以理喻的啰嗦,这些剧本把故事和行动变成了演说和修辞的附庸,有时甚至达到从舞台上完全排斥暴力、在许多情况下不让冲突双方主角见面的程度。作为在班克夏进行的另寻出路的试验,此类努力在今人看起来不免反常。
\r\r当悲剧确实值得搬上舞台的时候,它与对塞涅卡的模仿的联系,少于那种通过异种嫁接产生的悲剧。后一种是锡德尼之流的评论家们所鄙视的。吉拉狄·欣提奥开始进行了一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特别重要的试验。在他的第4个剧本《阿提勒》中,他给了它一个幸福的结局,并把它称为“tragedia di lieto fin”,意思是“结局幸福的悲剧”。坚巴提斯塔·瓜里尼领悟了其中的暗示,用了一个后来更受欢迎的名字“悲喜剧”来称呼它(来自普劳图斯《安菲特里翁》的开场白),并且在一个新剧本《忠诚的牧人》(Il pastor fido,1589)中具体应用了它。该剧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让·罗特鲁的《相像的人》(1637年)是对有关情节进行重新安排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对罗特鲁来说,《相像的人》就是他的“安菲特里翁”版,他将《疯狂的赫克利斯》中朱诺的开场白翻译出来,放在了《相像的人》的开头。然而,“悲喜剧”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喜剧气氛占优势,也不表明需有喜剧场面出现,它的主体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非喜剧的故事,看起来要以悲剧收场;可是,由于特殊的复杂性和故事出人意料的设计,最后没有以悲剧结束。后来,理论家们额手相庆,宣称这种新的作品类型是教信仰中一个信条的体现。该信条认为,人类所有偶然的行动,最终都是由上帝意志控制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上帝,而是《新约全书》殊的上帝,因为戏剧技巧遵循着神学的进步观念。可是,最后产生的,并不是对任何悲剧性结局的排斥,因为它在当时仍经常出现,而是它把这种结局和人们对此类作品的期望与喜剧中已经形成的人物、情节编排方法融合起来。“我们或许可以把欧洲的悲剧定义为:太伦斯的戏剧技巧和主题与高雅措辞的混合物,后者在传统的修辞理论中是常和悲剧联系在一起的。”(马丁·穆勒:《俄狄浦斯的后代们》,多伦多,1980年,第12页)到17世纪中期,当高乃依把他早年创作喜剧和悲喜剧的经验用来改写塞涅卡的《美狄亚》的时候,除了最学究气的古典派以外,这种混合物已经为欧洲所有的人接受了。
\r\r《美狄亚》(1635年)确实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画,使我们看到要对塞涅卡的新悲剧进行怎样的改造,才能把它变成值得表演的剧本。歌队完全被取消了;原来朗诵式的开场白(tirade,开场白现在由非正式的谈话替代)被削减,以大大增加对话的分量;老角色变得丰满起来,并增加了新角色;由于采用两条线索平行发展的方法,情节变得更加复杂,其最终的灾难似乎不是命运或者意志不可避免的产物,而是人物以及偶然事件相互纠缠的结果(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具——那件美狄亚用来杀死其对手克罗乌赛的致命的袍子——细节上的创新)。这些技术上的变革,和该剧主题的转变是不可分割的。高乃依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他把主题转到了年轻人恋爱的喜剧因素上,美狄亚—杰逊—克罗乌赛线索与另一个三角恋爱的线索:杰逊—克罗乌赛—埃勾斯(3)被交叉了起来(后者明显是喜剧式的),于是悲剧的主题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从老年人那里赢得年轻女性芳心的喜剧。这样一种对古典悲剧材料的现代化,后来变成了标准做法。由于引入了两个年轻的恋人,高乃依的《俄狄浦斯》变得几乎让人看不出原作的特色了。这两个人是提修斯和狄尔克,他们的婚礼成了全剧的结尾。莱辛强化了《菲德罗斯》(1677年),鼓吹年轻人恋爱的合法性,而原作强调的是这个年轻人对女性的厌恶心理。这样的改造在多样化的希腊悲剧中并非没有先例,但它们显然和塞涅卡一类的原作明显不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极大的背离。
\r\r然而,在悲剧发展过程中,塞涅卡式的悲剧并没有完全过时。高乃依的《美狄亚》中,就包含着原作中非常著名的段落,其中两行(第319—320行)是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
\r\rNérine. Votre pays vous hait, votre époux est sans foi;\r Dans un si grand revers que vous reste-t-il?\r Médée. Moi.
\r\r奶妈:你的祖国恨你,你的丈夫背信弃义;\r 在这样一场大转折中,你剩下了什么?\r 美狄亚:我自己。
\r\r波伊勒认为这是个庄严的时刻。“我自己”保留了原作中的回答“剩下的是美狄亚”所有的核心内容,它本身就激起了一大串著名的模仿者,“我还是安东尼”(《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第3幕第13场,第92—93行);“我仍是马尔菲女伯爵。”(约翰·韦伯斯特:《马尔菲女伯爵》,第4幕第2场第139行)这句话后来成了几乎所有有关美狄亚题材一个必有的特征,在19世纪德国作家的一个剧本中,她自豪地宣称,“Medea bin ich wieder”(意思是:我还是美狄亚。见弗朗兹·格里帕尔泽:《美狄亚》,第4幕)。T. S.艾略特援引这些仿作,以证明塞涅卡对欧洲文化影响的普遍性。他认为,这些仿作的修辞方式建立在特殊的斯多葛式、或至少是塞涅卡式的美学基础上,强调的是戏剧化的自我坚忍。它确实是塞涅卡式的,而且不仅仅因为哲学的原因。宣布个体独立是斯多葛派贤哲和塞涅卡式的恶棍共同的地方,他们鼓吹那种得到授权的辉煌自我能够向所有通行原则挑战的观点。没有任何一个古典作家,可能也没有任何一个古典戏剧作家,能够把这种野心用如此清晰和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塞涅卡的戏剧遗产中,这至今仍是最富有活力、最坚强的因素。一个好战的个体面向大众和喜剧的混乱提出挑战。悲剧技巧的完善,浪漫爱情的传播,都没有把这份遗产从悲剧中清除出去,人们只能用其他东西限制欧洲悲剧的这种特征,把它变得更加舒缓。
\r\r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自大狂似的庄严,其动力来自对一种不计代价的行动的狂热追求,这种行动会让人记住行为者的名字。在《图厄斯特斯》中,阿特里乌斯对此所作的说明也许是最精到的:
\r\rAge, anime, fac quod nulla posteritas probet,
\r\rsed nulla taceat. aliquod audendum est nefas
\r\ratrox, cruentum, tale quod frater meus
\r\rsuum esse mallet—scelera non ulcisceris
\r\rnisi uincis.
\r\r来吧,我的灵魂,干出那种后代不会同意、但谁也不会忘记的事情。有些罪恶是必须要做的,虽然它们残暴而血腥,就好像我的兄弟曾经希望他做过的一样。除非你超越了罪恶,否则你就没有对罪恶复仇。
\r\r(《图厄斯特斯》,第192—196行)
\r\r在雅典舞台上,即使最令人震惊的行为,也几乎不曾暗示有这种英雄策略式的动机。这是一种城邦从来不曾想象过的、非常反常的个人主义动机。在它的周围,聚集了大量夸张的词句(在希腊人那里只有很少的迹象),这些正是塞涅卡作为戏剧家的特点:
\r\rAequlis astris gradior et cunctos super
\r\raltum superbo uertice attingens polum.
\r\rnunc decora regni teneo, nunc solium patris.
\r\rdimitto superos: summa uotorum attigi
\r\r我脚踏星星,用我高傲的头颅碰触人类头顶上的天穹。现在,我掌握着王国的光辉,就是我父亲的王座。我赶走神灵,已经达到了我最大的愿望。
\r\r(《图厄斯特斯》,第885—888行)
\r\r话语中充满了胜利者的狂妄自负,这种过分的渲染摆脱了新古典主义戏剧技巧中令人生厌的背景,确立了自己在舞台演说中的地位:
\r\r我们准确的标枪在空中摆动,\r 枪尖犹如朱诺可怕的闪电,\r 它们曾在烈火和浓烟中烧锻,\r 对神灵的威胁比独目巨人的战争还要可怕,\r 进军时我们身披耀眼的盔甲。\r 我们将从天空中逐出星星,模糊它们的双眼,\r 让它们对我们可怕的武器颤抖和沉思。
\r\r(克里斯托弗·马洛威:《帖木儿》,第1卷第3章第18—24行)
\r\r近代早期的戏剧舞台上,这样直言不讳的说话是一个特色。一系列悲剧人物为傲慢的自我式的戏剧开辟了道路。
\r\r它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塞涅卡笔下的阿特里乌斯也许是最终标准,因为他显然用文学的语言,扫光了天上的太阳和星星。但马洛威的《帖木儿》紧随其后,而且确立了广受尊敬的原则:他修辞上的华丽,也就是他“让人震惊的语言”,和军事上连续取得的勇敢胜利是不可分割的。不可遏止的欲望和征服世界的经历,使该剧成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戏剧的开路先锋。可是,同样的修辞手法也可以为演讲者戏剧化的失败作为背景,犹如帖木儿本人最后不是亡于人间敌人之手,而是简单的死亡法则管住他一样:
\r\r来吧,让我们向天庭的权力挑战,\r 在天穹插上我们的黑条旗,\r 以显示我们对神灵的杀戮。\r 朋友们,我怎么办?我站不住了。
\r\r(《帖木儿》第5幕第3场第48—51行)
\r\r文艺复兴时代,在将某种近似于塞涅卡式的世界末日之类的事件编写成戏剧时,人们通过描写与事实相反的情形,来达到夸张的效果:
\r\r哀号吧,哀号吧,哀号吧!啊!你们都是些石头一样的人,\r 要是我有了你们的那些舌头和眼睛,\r 我要用我的眼泪和哭声震撼苍穹。
\r\r(《李尔王》,第5幕第3场第258—260行)
\r\r确实,正是在和那无法改变的现实的冲突中,这类话语才具有它最伟大的深刻和力量,远远超出它在塞涅卡本人作品中的力量。塞涅卡所写的是无所不能的幻想,而近代早期的戏剧家表现的是更加严酷的外部世界。
\r\r考验所采用的唯一最重要形式是复仇的故事:
\r\r大作的狂风,连同我的话语,\r 表达着我的悲痛,它们把光秃秃的大树连根拔起,\r 使花季翠绿的草原黯然失色,\r 山间的溪流,是我的眼泪。\r 它们冲破了地狱的青铜大门。\r 可是,我那饱受折磨的魂灵仍备受折磨,\r 带着破碎的哀叹,无尽的,\r 穿越山峰,飘荡在天际,\r 叩击着最美妙的天堂的窗户,\r 寻求正义和复仇。\r 然而,它们都在高高的天际,\r 还有钻石垒成的扶壁,\r 那地方简直无可逾越,它们\r 挡住了我的苦恼,让我的话无从传达。
\r\r(《西班牙悲剧》,第3幕第7场第5—18行)
\r\r这段话出自托马斯·库德的《希罗里摩》。该剧大体与《帖木儿》同时,声誉相当,其影响犹有过之。库德为英国的复仇剧确定了特殊的模式,把它变成了一种强制义务的悖论,使复仇者因其肩上的义务而与正常的人类社会脱离,复仇最终实现之日,也就是复仇者死亡之时。故事的类型尽管各不相同,有时是颠倒的,有时甚至遭到讥讽,但直到清教徒封闭剧院之时,它一直对英国悲剧有显著影响。詹姆士·舍莱的《枢密主教》(1641年上演)是该种戏剧光辉的终点,莎士比亚创造的最著名的人物形象讽刺了戏剧中的“吵闹”(《哈姆雷特》,第5幕第1场第284行),并对他的处境表示不满,但最终竟发现他自己也落得和此类悲剧中的人物同样的命运。
\r\r在大陆上的戏剧中,在维护“荣誉”的名义下,这类悲剧甚至取得了更大程度的支配地位。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会中,法国的古典悲剧和西班牙的喜剧都追随了高乃依和罗普·德维加,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自尊这个题材上。对于那些被侮辱者来说,荣誉表现得最为明显。就像在英国一样,行为一次次地表现为复仇问题,可是,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却颇为不同,因此所得到的结果也有异,其中既有荣誉悲剧,也有悲喜剧。这里我们举出两个最著名的例子:《熙德》(1637年上演)和《佩里巴雷兹》(约1606年上演)。为了为家庭所遭到的侮辱复仇,它们的主人公都选择了血腥的复仇,其行为竟得到宽恕,甚至得到君主的赞扬。在荣誉观念中,传统喜剧中女性贞洁所占的突出地位也大量进入这类悲剧中(佩里巴雷兹所以杀人,是因为对手试图他的妻子)。在法国的舞台上,荣誉的特殊性在于:它和爱情联系在一起(《熙德》一剧中,堂·罗德里格兹和齐美涅之所以不能结婚,是因为他们各自负有复仇的责任)。光荣的自我成为剧情的中心,它对主人公的要求非常严格,并常常让他陷入孤独,从而把社会和人际关系深刻地反映到戏剧的文本中。
\r\r大体说来,被布克哈特称之为“良心和自私的奇特混合物”(《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米德默尔英译,纽约,1958,第428页)的戏剧成为欧洲戏剧的一股主要潮流。美国的西部片或许可以被称为它在现代的后裔之一,与其把它说成像人们常说的善良与罪恶斗争的道德戏剧,倒不如说它是对男性自我认知条件与极限的探索。在17—18世纪的舞台上,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戏剧,它把新的背景与古典悲剧中的神话结合了起来: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圣经》和东方的编年史,近代早期欧洲本身的政治传说也越来越多但又恰如其分地被搬上了舞台。维托里奥·阿尔菲里(1749—1803)的悲剧集是这种趋势的代表,他写有《安提戈涅》、《奥瑞斯特》、《阿伽门侬》、《屋大维娅》、《索福尼斯巴》、《提摩里昂》、《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还有关于两个布鲁图的剧本以及一个《玛丽·斯图亚特》(后者已经是一个可敬的题材,首次由蒙克莱田将其写成剧本)、一个《帕齐家族的阴谋》(描写刺杀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一次著名阴谋)、一个《腓力普》,最后一个剧本写的是西班牙的腓力普二世和堂·卡罗斯,当然,席勒所写的该故事的剧本(《堂·卡罗斯》,1787年上演)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加著名的故事。作为记述“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学家之一,席勒把16—17世纪的欧洲作为他戏剧的主要背景,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德国古典戏剧的发展方向。他本人写过一系列剧本:《阴谋与爱情》(1783年上演)、《瓦伦斯坦》(1798—1799年上演)、《玛丽·斯图亚特》(1800年上演)、《威廉·退尔》以及一部未竟之作《德米特里乌斯》(恐怖的伊凡的儿子)。此外,歌德写过《埃格蒙特》(1788年上演),克莱伊斯特写有《汉堡王子弗里德里希》(1811年上演)。
\r\r这类剧本的精神是战争、宫廷政治中表现出来的贵族精神以及帝国野心,在他们傲慢的、违反事物规律的个性被磨灭的过程中,出现了周期性的危机。因此,“荣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表现阶级联系的词语,它是贵族认同感的某种形象化的总结,作为个人行事风格,可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佩里巴雷兹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由他的国王提升的,并像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一样行事)。从文艺复兴一直到19世纪,这类题材一直在戏剧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当时欧洲贵族所处地位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战士阶层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其成员也经常处在变动之中。但是,他们仍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和近代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可能是人们总是关注个人复仇的内在原因,因为复仇是国家最难废止的贵族特权之一(决斗仪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18世纪末,如在席勒和阿尔菲里的作品中那样,悲剧常公开站在唯意志论式的政治一边,因为与早期个人对抗暴君的复仇相比,此时的复仇更加普通,也更加公开化。
\r\r随着这类悲剧的发展,塞涅卡式的悲剧作为直接灵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确实,18世纪后期是塞涅卡作为悲剧作家声誉决定性的衰退时期。施赖格尔对他的戏剧的批评,把文艺复兴以来对他的崇拜颠倒了过来,并用下列相反的评论支配了随后一个世纪中对他的评价:塞涅卡的剧作“无可比拟的豪华与干瘪,性格和行动都不自然,违反了合宜原则,因此缺少戏剧效果。我相信,这些剧本根本就是给修辞学校用的,而不是用来表演的”(《戏剧艺术与文学史讲义》,约翰·布莱克译,伦敦,1846年版,第211页)。他支持一种广义的戏剧合宜原理。后来,这种合宜原则逐渐把塞涅卡悲剧中的大部分修辞手法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极端化赶出了戏剧舞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它在歌剧中找到了市场,其存在的时间也比在国内更长。(最早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是蒙特维尔狄的《波培娅的加冕》,除了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外,它还关注塞涅卡本人的死。当然,在整个18和19世纪,悲剧和歌剧的素材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叉的。)如果今天我们还能在悲剧中找到古典模式的话,那这种模式主要是希腊的,德国的古典主义实际上是该运动的第一波,它使希腊模式占据了决定性优势,并且自那时以来一直如此。
\r\r但是,在阿尔菲里的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到塞涅卡式朗诵体悲剧挥之不去的影子,而作为一个悲剧作家,席勒在《强盗》(1781年上演)的开头也采用了异常的夸张手法:
\r\r弗朗茨:哈,除了那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再想想看,死亡、天堂、永恒、诅咒,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你的嘴巴,此外还有别的吗?
\r\r摩西:此外再无长物。
\r\r弗朗茨:毁灭!毁灭!
\r\r尽管德国的戏剧非常尊崇亚提加的克制,但上述语言表明,它仍然发出了最后的怒吼,《拉奥孔》就是用塞涅卡的肺呼吸的。(4)
\r\r这样,德国的戏剧作家们也参与了欧洲那场最广泛的运动,歌德将其称为“魔鬼式的”自我,一种累赘而注定灭亡的个人主义运动。“So musst du sein,dir kannst du nicht entflichen.”(“你只能这样,除了你本人外,你无所逃避。”克里斯托弗·米德尔顿编:《歌德全集》,纽约,1983年,第1卷第230—231页)。德国的浪漫主义给这种个性化提供了我们的遗产所不能比拟的发展空间。它的戏剧也因此更加坚定地关注着那些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他们传播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对所有生物、甚至元素都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谁能知道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所有的道德力量联合起来,也无力与他们对抗。人类中比较明智的分子无望地试图使他们成为嫌疑犯。他们既是被欺骗者,也是欺骗者。可是,大众仍然受到他们的吸引。”(《歌德全集》,第5卷,第598页)
\r\r《强盗》中的卡尔·冯·摩尔是这类富有魅力的人物中的第一个,它深深扎根于文艺复兴有自我意识的恶棍传统中,“mein Handwerk ist Wiedervergeltung—Rache ist mein Gewerbe”(“我擅长的就是报复,复仇是我的职业”,第2幕第3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理查三世和麦克白的影子。然而,作为剧中无可争议的主人公,他的复仇对象是比他更加恶劣的兄弟,因此,他肯定了那种藐视一切道德的斯多葛主义,Sei wie du willt namenloses Jenseits—bleibt mir nui dieses mein Selbst getreu...Die Qual erlahme an meinem Stolz(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你这难以名状的未来——我只忠实于我自己……痛苦将磨损我的豪气!)席勒本人后来也在他认为不够成熟的作品中,发现它们所暗示的某些道德问题具有一定的风险,但他晚期剧本中更加富有节制精神的人物,仍然保持了同样的特点。英雄和恶棍都同样想达到一种纯粹的意志世界,Carlos nicht gesonnen ist, zu müssen(如果他愿意,卡洛斯不会和“必须”发生任何关系,《堂·卡洛斯》,第1幕第5场)。为了追求这个目标,甚至瓦伦斯坦也会用阿特里乌斯的口气讲话:
\r\rDoch eh ich sinke in die Nichtigkeit,
\r\rso klein aufhöre, der so großbegonnen,
\r\rEh mich die Welt mit jenen Elenden
\r\rVerwechselt, die der Tag erschafft und Stürzt,
\r\rEh spreche Welt und Nachwelt meinen Namen
\r\rMit Abscheu aus, und Friedland sei die Losung
\r\rFür jede fluchenswerte Tat.
\r\r但在我化为虚空之前,在我如此卑微地死去之前,我,这样一个曾经有过如此辉煌开头的人,要乘世界用那些每天都在出现和死去的可怜虫把我弄糊涂之前,让现在和未来的世界都带着仇恨记住我这个名字,让弗里德兰成为每一个可怕行动的记号。
\r\r(《瓦伦斯坦之死》,第1幕第7场)
\r\r此类题材的代表作当然是歌德的《浮士德》。它把浪漫主义的努力推向了顶峰,努力的目标是把可怕的个人主义从自我诅咒中解救出来。但所有这些努力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甚至将其推进到虚无主义(Nichtigkeit)的地步。在《彭特西勒娅》(1808年上演)中,克勒伊斯特将传统的爱情与英雄荣誉的冲突推到前所未有的血腥地步,结果是女主人公毁伤并杀死她的情人,陷入紧张症的恐怖之中:
\r\rJetzt steht sie lautlos da, die Grauenvolle,
\r\rBei seiner Leich, umschnüffelt von der Meute,
\r\rUnd blicket starr, als wras ein leeres Blatt,
\r\rDen Bogen siegreich auf der Schulter tragend,
\r\rIn das Unendliche hinaus, und schweigt.
\r\rWir fragen mit gesträuben Haaren, sie,
\r\rWas sie getan?Sie schweigt. Ob sie uns kenne?
\r\rSie schweigt. Ob sie uns folgen will?Sie schweigt.
\r\r她站在他的尸体旁,形象非常可怕,不发一言。那尸体已经被狗群嗅过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看。她肩上背着弓,胜利地离开了,走向那无限的远方,仍是默无一言。我们毛骨悚然,问她干了什么,她一言不发;问她认识我们吗?她还是一言不发;问她可愿与我们一起走?她仍是一言不发。(第23幕)
\r\r随后的相认一场根据《酒神》写成,但在《酒神》中,希腊人阿格夫最后是从他幸存的其他同伴那里寻求力量:“伙伴们,把我领到不幸的姐妹们那里去,她们曾经和我一起渡过流亡生活。”而德国的彭特西勒娅却顽固地保持孤立,最后通过某种纯粹意志的实现而死去:
\r\rDenn jetzt steig ich in meinen Busen níeder,
\r\rGleich einem Schacht, und grabe, kalt wie Erz,
\r\rMir ein vernichtendes Gefühl hervor.
\r\r如今我已能深入到我的心灵深处,就好像进入了矿井一样,为我自己发掘出毁灭的感觉,它犹如铁一样冰冷。(第24场)
\r\r尼采把克勒伊斯特和欧里庇得斯并提,但是,就其把无限悲哀作为心灵的高尚行动一点来说,克勒伊斯特与塞涅卡式的幻想关系更为密切。塞涅卡说:“这就是朱诺的生命,那时,宇宙毁灭了,众神混杂,自然一度停止存在,他安息了,退回到他的心灵深处。这正是智者所为……”(《书信》,第9卷第16章)。
\r\r类似的塞涅卡化并未得到承认,甚至是无意识的,传统的压力被广泛地吸收而不是回到起点(ad fontes)。如我已经指出的,在20世纪,塞涅卡的悲剧被某些先锋派戏剧视为戏剧之源。安托宁·阿陶德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他曾经把塞涅卡欢呼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而且确实是一个残忍派戏剧的先驱者、最优秀的“创作榜样”(威廉·维乌尔译,苏珊·宋塔编:《选集》,纽约,1976年,第307页)。他还写下了他对《图厄斯特斯》的出奇崇拜。在《坦塔勒的请求》(现已失传)中,他写下了他给塞涅卡的致敬词。可是,阿陶德的斗争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戏剧的文本化,特别反对那种华丽的朗诵体文风,而这些正是塞涅卡曾经给人们以灵感并帮助形成的。他呼吁复兴的是没有浮华文风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戏剧,塞涅卡似乎为他的原创提供了某些复原的力量:“在有序的讲话之外,我分明听到了混乱力量恶意的议论。”可是,从长时段看来似乎来自塞涅卡传统的东西,在现代戏剧舞台上却变成了另一个层次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好像那种把傲慢的自我推向成功的唯我论一样,完成的同时也意味着毁灭。
\r\r可以确定的也许是贝克特的例子,他笔下的哈姆“清了清喉咙,手指对着手指”,开始了他的开场白。他的话也许反映了我们上面一直在追溯的传统。“难道还有什么灾难……比我经历的更严重吗?”(《尾声》,纽约,1958年,第2页)同样的话我们可以在许多作家那里看到,如席勒的堂·卡洛斯说的是:auf disem großen Rund der Erde/ Kein Elend an das meine grenze。洛佩的堂·罗德里格说的是:No hay hombre tan desdichado/de polo a polo(El caballero de Olmedo),加尼尔的塞德西说的是:Voyez-vous un malheur qui mon malheur surpasse?(5)要特别表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粗鲁的话,可以借用约翰·马尔斯顿笔下的安东尼奥的话:“不要再说了,天哪!谁的痛苦有我多,我那赫拉克勒斯般的痛苦”(《安东尼奥的复仇》,第2幕第1场第133—134行)。尽管此类题材的多产是近代早期舞台的产物,但这些话的最终来源都是塞涅卡的“quae patimur vicere modum”(“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无以复加”,《阿伽门侬》,第692行),它们都把痛苦和塞涅卡式自我实现之间的较量联系起来。哈姆这个永恒的未来演员,既再现了这种实现的情景,又极大地阻碍了它的发展。上述引文中的省略是为了掩盖舞台上的中断(法文该行甚至更加结巴),可以设想,从修辞学上讲,紧随其后的是那个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的回答——“毫无疑问”,从而把演讲人和人类的其他成员又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上。
\r\r这种模式还在不断再生,“越是高大的人,就发育得越充分,但也越空虚。”话语的扩张显示了思想的贫乏,当哈姆以干瘪的形态表现古代支配的范型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近代的阿特里乌斯站在宇宙的大舞台上,那里天堂之光尚未充分散射出来便已消退。“从南极到北极,到处是轻度的黑暗。”或者用更加常见的法语来说是:Noir clair. Dans tout l’univers(黑暗式的明亮,然后是彻底的黑暗)。
\r\r Further Reading\r\rThe entire Roman dramatic corpus is serviceably translated in The Complete Roman Drama, ed. George E. Duckworth, 2 vols. (New York, 1942). Livelier and more contemporary versions of individual comedies are available from numerous translators; two collections edited by Palmer Bovie deserve special mention: Five Roman Comedies (New York, 1970) and The Complete Comedies of Terence (New Brunswick, NJ, 1974). A delicately personalized version of Plautus’ Rudens forms the twenty-first section of Louis Zukofsky’s long autobiographical poem ‘A’ (Berkeley, 1978). Senecan tragedies have in general attracted less attention from translators; E. F. Watling (Harmondsworth, 1966) and Frederick Ahl (Ithaca, NY, 1986) have recently produced modern versions of a few of them. The complete tragedies are available in the Elizabethan translations—less impressive than they ought to be—collected by Thomas Newton (1581) and reprinted in several forms this century. Douglass Parker’s courageously intemperate version of Thyestes may be found in The Tenth Muse, ed. Charles Doria (Athens, Ohio, 1980); Ted Hughes’s arresting adaptation of the Oedipus, written for Peter Brook’s stage production, is available with an interesting preface by the director (Garden City, NY, 1972).
\r\rOn Roman comedy, George E. Duckworth, The Nature of Roman Comedy (Princeton, 1952), remains standard and compendious, and has a fair section on influence. Recent attempts to sum up the genre in more sophisticated terms include David Konstan, Roman Comedy (Ithaca, NY, 1983), Erich Segal, Roman Laughter: The Comedy of Plautus (Cambridge, Mass., 1968), and Sander Goldberg, Understanding Terence (Princeton, 1986). For detailed looks at Roman comedy in the Renaissance, see Marvin Herrick, Italian Comedy in the Renaissance (Urbana, Ill.,1960), Douglas Radcliff-Umstead, The Birth of Modern Comedy in Renaissance Italy (Chicago, 1969), and Leo Salingar, Shakespeare and the Traditions of Comedy (Cambridge, 1974). On the commedia dell’arte, Allardyce Nicoll’s The World of Harlequin (Cambridge, 1963) is still the best introduction. The course of tragicomedy as a deliberate generic experiment can be followed in Herrick, Tragicomedy: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in Italy, France and England (Urbana, Ill., 1955).
\r\rImportant summary statements on Roman tragedy include C. J. Herington, ‘Senecan Tragedy’, Arion, 5(1966), Norman T. Pratt, Seneca's Drama (Chapel Hill, NC, 1983), and Thomas G. Rosenmeyer, Senecan Drama and Stoic Cosmology (Berkeley, 1989). For an ambitious look through some of the lenses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see Charles Segal, Language and Desire in Seneca's Phaedra (Princeton, 1986); the essays collected in Seneca Tragicus, ed. A. J. Boyle (Berwick, Victoria, 1983), are also a useful sampling of the current approache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Seneca’s theatrical Nachwirkung is Der Einfluß Senecas auf das europäische Drama, ed. Eckard Lefevre (Darmstadt, 1978), with extensive bibliographies organized by nation; see also the essays, in several languages, in Les Tragédies de Sénèque et la théâtre de la Renaissance, ed. Jean Jacquot, (Paris, 1964), and , in English, H. B. Charlton, The Senecan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Tragedy (Manchester, 1946). Martin Mueller’s Children of Oedipus (Toronto, 1980) is unsystematic in its coverage and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the afterlife of Greek tragedy, but nevertheless illuminates Seneca’s case in particularly useful ways. Many of the arguments advanced above are set out in more detail in Braden, Renaissance Tragedy and the Senecan Tradition (New Haven, 1985). Much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scussion is in article form, see especially T. S. Eliot’s essays, ‘Shakespeare and the Stoicism of Seneca’and ‘Seneca in Elizabethan Translation’, in hi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1950), and G. K. Hunter, ‘Seneca and the Elizabethans: A Case Study in “Influence”’, in his Dramatic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 (Liverpool, 1978).
\r \r\r(1) 意思不详。
\r\r(2) 在英语中,伊凡雷帝叫Ivan the Terrible,因此汉语中有时也译为“恐怖的伊凡”。
\r\r(3) 在希腊神话中,杰逊去科尔启斯取金羊毛,得美狄亚之助成功后,二人结为夫妻,定居科林斯。后杰逊移情别恋科林斯公主,欲逐美狄亚。美狄亚祈求无效,杀二子后逃亡雅典寻求埃勾斯庇护。
\r\r(4) 意思是《拉奥孔》的精神是塞涅卡的。
\r\r(5) 上述引文意思大致相同,都是说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无以复加。
\r\r\r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7-13处女摘花(真实处破女摘花过程)
- 06-26王俊凯喜欢谁(王俊凯承认有喜欢的女孩)
- 07-06阳女木三局(阳女木三局是什么意思)
- 07-05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什么级别(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级别)
- 06-29射手座女星(世界十大射手座女明星)
- 07-06男人靠女人(为什么男人靠女人被指吃软饭)
- 06-13八字脚铐(武则天发明的七大酷刑到底有多残忍)
- 06-29女人梦见死尸什么预兆(女人梦见好多死人有什么寓意)
- 07-14右锁骨有痣的女人(女人右锁骨有痣代表什么)
- 07-04帝旺(帝旺代表什么意思)
处女座最新文章



- 01-02217是什么意思(217是什么意思爱情含义)
- 01-02正缘画像(正缘画像测试免费)
- 01-02愚人逆位(愚人逆位爱情)
- 01-02瓷都算命免费(瓷都算命免费算命)
- 01-02金牛男断联真实心理(金牛男不可能复合的表现)
- 01-02朗字五笔怎么打(望字五笔怎么打)
- 01-02射手男一旦爱上白羊女(射手男一旦爱上白羊女的表现是什么)
- 01-02六十四卦图文详解(伏羲六十四卦图文详解)
- 01-02上升星座怎么看(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怎么看)
- 01-02楞严咒佩戴后很倒霉(楞严咒吊坠的作用和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