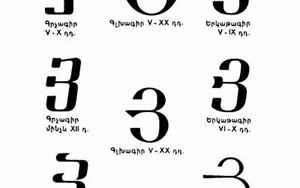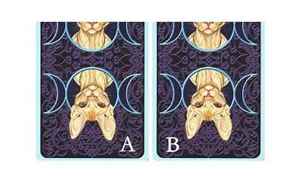林间空地(林间空地英文诗歌)
河北围场:山上绿树成荫 山下林地生“金”
中新网河北新闻6月26日电 (王东岭)近日,走进河北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下伙房乡哈巴气村一个叫“下北沟”的山里,青山巍峨,万木吐翠。
“我们村在40亩荒山里栽植1500棵果树,在果树下间作30亩芸豆,芸豆亩产可达300斤,市场价格在每斤5元,秋季收获时节,仅芸豆一项可以收入1500元。”哈巴气村村民孙龙高兴地说。
下伙房乡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把林下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村集体流转土地50余亩,打造了哈巴气村和东沟村两个果树种植示范基地,发动乡村干部、公益岗、村民栽种“龙丰”“鸡心果”“123果树”(也叫“金红苹果”)共计2000余棵,不断做大“林”文章,做活“林”经济、提升“林”效益,实现林下生绿又生“金”,充分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成为经济发展优势。
在哈巴气村范文伍的苗木基地,百余棵造型松已然成型,翠绿挺拔,在阳光的照射下,洋溢着一片绿意,给人一种置身绿海的感觉。
范文伍是该村有名的苗木种植大户,凭借着十余年的苗木种植经验,目前已有苗木基地200余亩。随着苗木市场需求的转变,范文伍不断更新观念,通过培植造型松提高苗木的附加值。
近年来,围场积极探索适宜本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狠抓供给侧改革,调优产业发展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大力发展以干鲜果品、木本油料、园林绿化苗木、木本花卉中药材等为主的经济林产业。引导帮助群众利用林间空地、森林边缘地带,发展林药、林菌、林禽等林下经济,将林下资源变成菜篮子、药园子,同时,采取“企业带动、村集体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带动全县1.6万人从事经济林种植,发展经济林194万亩。(完)
塞罕坝的年轻人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图①:塞罕坝机械林场风光。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图②:范冬冬在测量树木生长情况。 图③:张立在验收木材。 图④:袁中伟在整理林业数据。 制图:潘旭涛
初春时节,冰雪尚未消融,阳光照射在冰冷的雪原上,雪映青松,韵味无穷,恰似一幅泼墨山水画。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北部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每年可涵养水源量2.84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9.84万吨,牢牢守护着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
然而,这片生机勃发的土地,60年前却是荒寒冷寂、黄沙漫漫。为改变当地自然风貌,1962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近60年间,三代塞罕坝人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与毅力,成功将“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坡变为万亩林海。
如今,绿色“接力棒”已传递至“80后”“90后”中青年林场职工手中。紧跟前辈的脚步,“林三代”们迎接新机遇、不畏新挑战,在续写塞罕坝“绿色传奇”的同时,用青春奏响激昂的奋斗乐章。
第三乡分场范冬冬:
每天跑山看树才踏实
去年入冬以来,塞罕坝连下几场大雪,积雪最浅处也有10多厘米厚,这对缓解防火压力作用极大,但塞罕坝第三乡分场副场长范冬冬仍不敢有丝毫怠慢。
3月11日,天刚蒙蒙亮,他便爬下床,简单吃过早饭,裹上棉衣、穿上棉靴,开始了新一天的跑山。36岁的范冬冬,脸上透着“高原红”,不算高的身材在雪地上矫健前行。
如往常一般,范冬冬穿梭在落叶松、樟子松林中,仔细察看林间有无火情,护栏是否破损,开春用于造林的苗木有没有被积雪压断……参加工作以来,他的巡山日记写满了关于林子的大事小情。
范冬冬是河北石家庄人,2007年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塞罕坝。15年间,他在这里安了家,并一步步从最初的技术员,成长为主管造林与育苗的中坚力量。
尽管身份在变,但范冬冬对林子的感情始终如一。
有一段时间,他被安排分管财务工作,但还是天天跑山。“我就是坐不住办公室。”范冬冬说着就嘿嘿一笑,“我没有睡懒觉的时间,每天不到林子里看看,我心里就不踏实。”
对于范冬冬来说,2011年是他工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这一年,塞罕坝正式启动攻坚造林。作为营林方面的技术骨干,他一直全程跟班作业,造林工程到哪,他就跟到哪。
范冬冬介绍说,2011年之前,树苗容易活的坝上地块,造林任务已经顺利完工,剩下的全都是山高坡陡、立地条件极差的“硬骨头”地块。“有的土壤厚度只有几厘米,有的坡度甚至达到46度,难度超乎想象。”
因为坡陡地滑,机械无法上山作业,树坑只能靠人工一镐一镐刨出来。头一镐下去,便震得范冬冬双手生疼,待扒拉开几厘米厚的土层一看,下面拳头大小的石砾一个挤着一个。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难怪50多年了,这里没种活树。”
眼看坡面直栽难度过大,范冬冬与同事们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换种思路——待平地育苗成功后,再移植上山。
“苗木选择可有讲究了,要选‘矮胖子、大胡子’,也就是株植粗壮、根系发达的,这样更易于成活。”范冬冬说,“苗木运输时还要用保湿透气的包装物打包并浇透水,不能重压、日晒,还要保湿、防捂。”
接下来,运苗又成了难题。
一株容器苗浇透水后足有七八斤重,一个骡子要驮两筐苗,踉踉跄跄爬一段,就累得呼哧带喘,甚至还有滑坡的危险。骡子上不去的地方,就只能靠人工背运。一人背上十几棵,筐上的麻绳在大家后背上留下了一道道勒痕。
“在山上作业,最怕的就是看见云朵飘来,因为一片云就可能带来一场雨。”范冬冬说,很多次,他就头顶着塑料布,蹲在树下苦等雨停。带的热水若是喝光了,就只能用凉水泡方便面充饥。
“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这是塞罕坝攻坚造林秉持的理念。现如今,98.9%和92.2%的历史最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推进塞罕坝人的美好愿景走向现实。
身为技术人员,这两年,范冬冬又开始了丰富塞罕坝树种的探索。他请新疆同行邮寄西伯利亚云杉树籽,并引进东北地区的水曲柳、黄菠萝等树种。
“哪怕失败一百次,有一次成功也值了!”范冬冬坚定地说,引进树种的事儿要坚持做下去,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林子的稳定性,减少病虫害等问题发生。
随着同事的呼喊声在远处响起,范冬冬满怀歉意地打断了采访:“不好意思,咱们下次再聊。”他又一头扎进林子,继续“跑山之旅”。
北曼甸分场张立:
爱上这里的执着与坚守
塞罕坝有多冷?塞罕坝北曼甸分场的“90后”女职工张立向记者讲述了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
那是2020年11月,她上山到营林区,入库验收木材。此时,正是坝上最冷的时候,西北风刮起,砸在脸上生疼,雪深的地方已经没过膝盖,偶尔一不小心掉进雪窝,靠同伴搀扶才能拔出腿来。清点木材时,她一边用笔作记录,一边冻得跳起“踢踏舞”。
“当时气温已下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眼睫毛上都是冰,冻得我鼻涕直流、手脚发麻。”张立说,“好在当时已经工作一年多了,对这种工作条件已逐渐适应。”
张立是土生土长的围场人,2019年10月,林学专业毕业的她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名年轻建设者。
“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但终究抵不过心中的那份牵挂。”谈到自己的选择,这位文静又稍显柔弱的姑娘一脸平静。问及做出选择的原因,她说这是自己的初心,也是受前辈们的影响。
“小时候,就觉得这里的景色太美了,随便怎么拍照都很好看。”在张立的记忆中,幼时的自己特别向往坝上的生活,一有空闲就会来这里游玩,“上大学后,虽然离家远了,但每次放假回来,我都要到林场转转。”
深入了解林场历史后,她决心像老一辈务林人一样,做一粒绿色的种子,扎根这片绿海、守护这片绿色。
2019年,初到北曼甸分场的张立,便下沉到一线——石庙子营林区,从事营林造林工作。起初,她感觉身边一切都是新鲜的,浑身似乎有用不完的力量,可慢慢过了几天,热情与信心开始消减。
“营林工作需长期在户外,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条件很是艰苦。”张立坦言,那段时间,自己动摇过、纠结过,甚至还在被窝里偷偷掉过眼泪。
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台阶营林区主任于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她。
2006年,于洋主动放弃了留在部队的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塞罕坝。在营林区,夏季,他与强烈的紫外线为伍,冬日,他又与呼呼的西北风为伴,生产繁忙时,他从清晨6点就要开始工作,直到晚上8点才能下山,就连妻子生产,他也仅是请了3天假。基层工作15年,他没有一句怨言,也从未后悔过。
“和于洋主任那时候的工作条件相比,现在的我,在通水、通电、有暖气的营林区里工作生活,还有什么理由退缩呢?”张立暗下决心:“不能愧对自己的专业,一定要为家乡奉献自己的力量!”
站在泥泞的土地里,她主动学习“三锹半植苗法”栽植;穿梭在挺拔的树木间,她尝试运用“去密留疏、去小留大、去劣留优”原则进行选择……一年时间里,她走遍了管辖区域内的每一片林子,学会了如何识别树种,见证了每一株树苗的成长。
2020年,她调回到场部工作,被分配安排至经销股。这让张立远离了大部分户外工作,更多时候是在办公室做表、入账、归档,但她依旧兢兢业业,没有一丝放松。
“我一直在思考,还能为林场做些什么?”张立认为,“林三代”们要传承塞罕坝精神,继承老一辈务林人对林业事业的执着,用一个个细小进步、一天天认真负责、一次次优异成绩,共建美好的塞罕坝。
“作为一名大学生,回到这片土地,就应该起到自己的作用,将学到的林业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守护这片林子。”张立说。
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袁中伟:
当好塞罕坝的“森林医生”
3月12日清晨,迎接着第一缕阳光,一棵戴着“雪帽”的云杉幼苗热情地张开绿枝。
望见此景,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技术员袁中伟小心扒开积雪,仔细观察着茎干情况。“这个季节降雪还比较多,山鼠都藏在雪里不出来,时常啃咬树皮。”说罢,他又沿着山鼠脚印,在林间空地布下鼠夹、架起钢丝索套。
“森林医生”——“80后”袁中伟喜欢这样形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以此为荣。2011年,毕业于新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学专业的他,决定到塞罕坝一展所长。
给森林“看了10年病”,但袁中伟的脸上并没有像其他务林人一样透着“油松黑”。他调侃道,因为每天都要在林间穿行20多公里,树荫遮住了太阳,根本晒不到。
冬季穿行是为了防鼠,其他三季则是为了防虫。
虽然森林覆盖率高,但塞罕坝树种单一、成熟林面积较大,是适生虫害的先天温床。因此,最初几年的春夏之交,袁中伟经常与同事们起早贪黑,每天凌晨3点到达作业地块,身背约30公斤重的药剂和设备,举着喷头并排前进,漫山遍野地喷洒药物。
因为虫情年年都在变化,袁中伟不断观察各种害虫的生活习性,提前制定应对预案。
2019年5月,他发现森防站缺乏落叶松鞘蛾生活史资料,于是就从阴河分场红水营林区取来幼虫,放在监测点进行人工饲养。小米粒大小的幼虫,肉眼极难看清,但袁中伟坚持每天观察一次,次次都要核对数量,只为精准判断幼虫高峰期。
“4月底防治鞘蛾,5月防治尺蛾,5月下旬到6月上旬防治松毛虫……”这些防治计划,袁中伟已是倒背如流。在他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塞罕坝森防站先后主持完成了《白毛树皮象预测预报技术规程》等5个地方标准,在全省组织的森防联合检查中多次荣获第一。
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病虫害防治手段得到更新发展,塞罕坝也开始利用无人机防治森林病害。
2020年6月,袁中伟熟练地操作无人机,在三道河口分场周边林区急速升空,通过高清摄像头,巡查林木病虫害防治进展。“无人机一次能防治十几亩地,特别适合树林茂密、地势陡峭等人进不去的地方。”他告诉记者。
“学驾驶无人机可比学开车难多了。”袁中伟说,无人机在空中并非说停就停,而是上下飘浮、动态摇摆的,既要学习高度、风向等操作知识,还要上机模拟飞行,锻炼手感。此外,操作者的方向感也极为重要,不然,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坠机”。就这样,袁中伟没日没夜地练了20多天,最终顺利通过考试。
据了解,借助“天、地、人”立体化防治方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塞罕坝机械林场成功建立起高效的管控防治体系。
“这几年塞罕坝的林子很健康。前辈们把林子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负起责,要把这片林子守护好。”袁中伟语气坚定地说。
山区野外种植天麻,场地选择是否合理是成败的关键,应注意些啥
山区种植天麻,很多农户喜欢在野外的林下或露地栽培。调查发现,场地选择是否科学合理,是野外种植天麻成败的关键。不少农户就是因为选址不当,导致天麻种植后管护难度大,技术难到位,病虫杂菌多,产量效益低。山区野外种植天麻,到底应该注意些啥?
天麻
一、管护要便利有的农户沿用过去做法,将种植地点选择在位置偏远、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中。这样做的好处是种植天麻需要的菌材、腐殖土等资源丰富,场地不需要租赁费用,种植后任其自然生长,后期管护费用低,但问题是在种植、收获过程中,各种材料和产品进出运输难度大,日常看护、管理困难,产量不稳定,基本靠天收,且成品麻遭野猪等多种野生动物取食、破坏,他人盗挖的风险也很大。
另外,近年来山区人口急剧外流,在深山老林中种植天麻雇工难、工价高,管理难、费工高,其综合成本明显偏高,经常得不偿失。
因此在野外种植天麻,必须根据当前山区人口外流、劳力偏少实情,把管护便利程度放在重要位置,将种植地点尽量选择在交通便利、管理方便,附近有清洁水源的地方,以便加强日常管理,在有效控制成本同时提高单产效益。
村民种植天麻
二、海拔要适中天麻较耐低温,性喜凉爽湿润气候,生长期间对温度要求较为严格。冬季温度低时,天麻生长停滞,处于休眠状态。春季温度升至15℃左右时,天麻开始萌动生长。随着温度升高,天麻生长逐渐加快,20~25℃时生长速度最快。夏季温度升高至30℃时,天麻生长受阻。如果温度持续升高,天麻不仅不再生长,还易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高温、高湿,对天麻与蜜环菌的生长均极为不利,很容易造成烂麻。
像秦巴山区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境内海拔高差悬殊、立体气候明显。海拔越高,夏季气候越凉爽,空气与土壤湿度也高,菌材与腐殖土等资源也非常丰富,气候与环境条件均适合天麻生长,但冬季温度低、持续时间长,天麻有效生长时间较短,年生长量受到限制。
海拔越低,夏季温度越高,而且高温持续时间也越长,同时还会经常遭遇到持续干旱或雨涝等灾害性天气,天麻有效生长时间也短,而且容易出现烂麻。
因此,该地区在野外种植天麻,最适合的区域就是海拔600~800米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二高山地区;其次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地区;低山因种植风险较大,最好不要在野外种植。
另外,在野外种植天麻,高山应选择较温暖的向阳坡地,采取地表或半地下式栽培,这样土壤春季升温快,有利于延长生长时间;二高山应选择半阴半阳、光照适中的缓坡地,采取半地下式栽培;低山则应选择在夏季凉爽湿润处,采取地下式栽培,以利降温保湿,同时采取搭设荫棚、覆盖落叶、高温喷水等辅助降温措施,确保天麻能够安全越夏。
采收天麻
三、林种要合适山区植物种类繁多、林种异常复杂,有针叶林、有阔叶林,有高大乔木、有低矮灌木,有纯林、有杂灌。野生天麻多生长在枯枝落叶较多、土壤比较疏松、腐殖层较厚的稀疏阔叶林下或林间空地、林地边缘,尤其是栎木林(农村俗称橡子树)下野生天麻较多。
在野外种植天麻,多以林下种植为主,要尽量选择与野生天麻生长类似环境。最好选择在山区生长旺盛、分布较广的稀疏栎木林下种植,这种林下落叶较多、腐殖质含量较高,有的地方土层较厚,特别适合天麻及其伴生菌(蜜环菌)生长,而且林间杂物少,杂菌害虫少,场地容易清理,种植天麻所需的菌材、腐殖土等可以就地取材。
如果树木过于茂密,可适当进行修枝或间伐,使其光照与通风符合天麻生长条件;如果树木过于稀疏,高温季节可酌情搭设阴棚进行遮阴。
其次,可选择在其它疏密适当的阔叶林下种植。茂密的针叶林下阴冷潮湿,土壤养分贫瘠,不宜选做天麻种植场地。含有油脂的树种下也不宜种植天麻。另外,林种复杂、林间杂物多、荆棘藤蔓丛生的地方,场地清理难度大、费工多,也不宜种植天麻。
四、土壤要疏松天麻生长所需养分主要来自于菌材,虽对土壤养分要求不是很高,但对土壤环境要求却很高。一要疏松透气;二要相对湿润,含水量保持在45~60%为宜;三要尽量少带病虫、杂菌;四要ph值中性至微酸性。
天麻虽然喜湿,但土壤湿度过高对其生长不利,容易出现烂麻。如果种植地渍水,更会对其造成致命危害。因此种植天麻的场地,必须选择排水良好、不易渍水的坡地、缓坡地或坪地,低洼潮湿的地方不能种植天麻。
种植天麻的土壤,首选阔叶林下的腐殖土,这种土壤不仅团粒结构好,疏松透气,酸碱度适宜,病虫杂菌少,而且富含天麻和蜜环菌生长所需的养分,最适合天麻生长。
其次是泥沙土或沙壤土,这类土壤虽养分含量低,但透气性好,病虫杂菌少,也适合天麻生长。再次是林间疏松的黑沙壤、砂质黄棕壤,这类偏砂质土壤种植天麻,管理得当也可获得较高产量。透气性较差、不易沥水的粘重土壤,均不宜用来种植天麻。
另外,长期耕种施肥的熟地、菜园土虽较为疏松肥沃,但其中病虫、杂菌较多,也不能用来种植天麻。
种植天麻的土壤,要尽量就地取材以降低成本。如果选定的种植场地没有合适土壤,应在附近阔叶林下收集腐殖土,或用泥沙、河沙等对原土壤进行改良,使其符合天麻生长条件。
林下种植天麻
五、场地要轮换天麻不耐重茬,如果在同一块地多年重复种植,会导致病菌、害虫逐年积累,对天麻和蜜环菌生长的抑制作用逐年增强,天麻产量、品质逐年下降,甚至出现绝收。
山区山场辽阔,在野外种植天麻可以选择的余地较大。但有的农户为图省事,选择在过去种植过天麻的地方重茬种植,以为这样比选择新址更加稳妥,却因重茬种植导致天麻生长不良、效益不佳。
因此,在确定天麻种植场地时,要选择在未种植过天麻的地方,或在种植过天麻的区域附近选址。地块选定后,要对场地和周边环境进行清理改造。先清除地表杂物,可能渍水的要开挖排水沟,可能受旱的要引水或开挖蓄水池,有条件的可安装微喷灌设施。在林下种植天麻,还要特别注意做好白蚁和鼹鼠(俗称“地老鼠”)的防治工作。
一个场地种植1~2年后,再种天麻必须转移到邻近地块或另觅新处,原地块可改种黄精、玉竹、白芍等其它中药材,通过轮作换茬减少病虫,提高天麻产量与效益。
塞上“明珠” 三秦“千金”
对榆林产生兴趣,皆因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片首的那段话:“谨以此片献给路遥故乡陕西榆林的父老乡亲……”
榆林地处陕、甘、蒙、晋四省交界处,战略位置重要,战国时期魏国的长城就修建于此,是真正的边塞要地。榆林是陕西最北端的城市,距西安670公里,距离最近的中心城市延安也有267公里。孤悬陕西之北,可谓偏远。又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想必荒凉。从延安向北,地貌之色渐次单调,黄色的土原,黎黑的山岩,树木稀疏,草色暗淡,甚至有几处石山寸草不见!唯有公路两侧用来防尘、防燥、防光的柏树算得上一点亮色。但谁都知道,在这干旱之原,栽种这些绿色屏障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越向北走,逾见其荒凉。举目四望,由近及远,风景迥异。公路边的柏树林,成排成行但不成林的杨树,低矮的灌木红柳棵子,紧趴在沙丘上的不知名的黑黄色蒿草。这蒿草已是沙漠里最独特、最珍贵的“主人”了,枝干如莲花一般匍匐在地,牢牢地压着身下的沙土。这蒿草又不像草坪般完全覆盖在沙丘上,如同金钱豹身上的斑点,散落在广密的沙丘之上,一阵风来一阵沙尘。
看见榆林、疲惫暗淡的眼神立时兴奋而发亮。杨柳掩映,楼房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宛若丑小鸭里的白天鹅,亭亭玉立,笑意盈盈。城外的杨柳是榆林城的“防护神”,杨柳的“品相”颇为独特。杨树,笔直、高大,像俊俏的北方少女;柳树,树干粗壮,树干上长出的枝条犹如冲冠的怒发,极像是健壮的蒙古汉子。
榆林城清新、整洁、俊朗。楼房大都很新,也不拥挤,街道宽阔、街景靓丽。街道上的绿化苗木与众不同,每10米左右栽有一棵白杨树,疏朗、挺拔。围着白杨树的是挤挤挠挠的绿化灌木,灌木有两种,一种枝叶泛黄,太阳下发出金灿灿的光芒;一种枝叶接近紫红,宛如红唇烈焰。两种色彩并肩而立,甚是奇异,惹人喜爱。街道上人来车往,却并不拥堵,相比较于大都市,反而有几分都市里热闹中的宁静。
榆林城区长城路上,有一段五、六百米长的“古长城”。虽然是后来重修的,但墙面斑驳之色,告诉人们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沿拱形门走进长城,却是另一番天地,城墙内是几条繁华的商业街。利朗、九牧王、老板电器等品牌店分布其间,门面招牌都气势宏伟,与其身份匹配。不远处还有一个不太大的休闲广场,有花木亭台、绿地景观,一些人带着孩子在玩乐。古城墙昭示着榆林的“古老”和沧桑,那些高楼背后的旧居和小巷记载着榆林的历史,但我们没有看到,只看到榆林的年轻与俊俏,足见榆林近年的高速发展。榆林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结合部,西北紧邻毛乌素沙漠,是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但整区却是如此秀美,秘诀还是那个哲理:有水就有生命。榆溪河自北向南穿城而过,城区像两只巨臂紧紧拥抱着这座城市的生命之源。榆溪河水的流量与我们的洛河差不多,滔滔河水给榆林带来了勃勃生机,使榆林成为边塞之地耀眼的明珠。
榆林的身份不仅是“明珠”,还因其拥有丰富的资源而成为富甲三秦的“千金”。
“榆林市全市已发现8大类48种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岩盐等能源矿产资源富集一地,分别占全省总量的86.2%、43.4%、99.9%和100%。平均每平方公里地下蕴藏着622万吨煤、1.4万吨石油、1亿立方米天然气、1.4亿吨岩盐。资源组合配置好,国内外罕见。
煤 炭预测6940亿吨,探明储量1500亿吨。全市有54%的地下含煤,约占全国储量的五分之一。天然气预测资源量4.18万亿立方米,已探明气田4个,探明储量1.18万亿立方米;石油预测资源量6亿吨,探明储量3.6亿吨;岩盐预测资源量6万亿吨,探明储量8857亿吨,约占全国岩盐总量的26%,湖盐探明储量1794万吨。此外,还有比较丰富的煤层气、高岭土、铝土矿、石灰岩、石英砂等资源。 [29
榆林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下拥有10亿元的地下财富,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占全国1/3。每平方米土地下平均蕴藏着6吨煤、140立方米天然气、40吨盐、115公斤油。”(——引自百度百科)
这些“黑金”、“白银”上天所赐,得天独厚,令人艳羡,使榆林这颗塞上明珠光芒万丈,是三秦这位富家“千金”光彩夺目。
维舟:桑树是神树,蚕是神虫,丝绸由此而来
中国是发明丝绸的国度,西欧诸语言对“丝绸”的称呼(如英语silk,古法语seie,德语Seide,中古拉丁语seta)基本可确信都源自经由丝绸之路上的草原民族辗转借入的汉语词“丝”,中国人也因此被古罗马人称为“丝国人”(Seres)。这在当时的确是中国文明一项极不寻常的特点,因为自从人类脱离野蛮状态制作衣裳起,世上绝大多数部族穿的是动物皮毛(或使用毛纺织技术),东亚古代还长期利用植物纤维(麻、葛或芭蕉,棉纺织则相当后起),但利用蚕丝的,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就只有中国人。
虽然远古时代的中国人穿衣也兼用皮毛和植物纤维(《韩非子·五蠹》称尧“冬日麑裘,夏日葛衣”),但对后来的中国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无疑是丝绸。这不仅体现在“丝绸之路”上对外交流时,甚至在汉字本身上面就能看出来:以丝为偏旁的汉字至少有284个,不仅丝织品,连通用纺织技术的许多术语(如“纺”、“织”、“纱”、“绣”),以及许多抽象概念(红、绿、纯、继、绝等)都是由此而来,可说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人也确实不曾轻视丝织的重要性,长久以来将之归为黄帝的贡献,意在归结为圣王使人免于“未有衣服”的野蛮状态;唐代以降,世人大体一致明确将之归于黄帝后妃嫘祖的功绩,不过现在看来,这很难说是信史。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挖掘山西省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发现长约1.36厘米的半个蚕茧,经与昆虫学家刘崇乐共同鉴定,确认是已知最早得到利用的蚕茧——距今约5600-6000年。虽然这切开的蚕茧不一定是用于丝织,但至少表明已进入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据传记载夏代物候的《夏小正》中,已有“三月,摄桑委扬,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的记载。一个随之而来的棘手问题是:正由于蚕的驯养比甲骨文的诞生还早了至少两千年,因此丝绸的起源一直是个谜团。朱新予主编的《中国丝绸史》(通论卷)根据唯物史观,将之归结为桑蚕资源的存在、发达的古文化和社会需求这三个背景条件。但这些相关观点都忽略或低估了在丝绸起源这一问题上的宗教意味。
桑葚
作为神树的桑树
我们须理解:在上古人的心目中,桑树乃是一种神树。李时珍《本草纲目》木部卷三六木之三“桑”条引徐锴对《说文解字》的注解:“桑,音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名,其字象形。桑乃蚕所食,异于东方自然之神木,故加木于下而别之。又引北宋苏颂《本草图经》语:“方书称桑之功最神,在人资用尤多。”
正如Nell Parrot所说,“不存在什么对树本身的崇拜;在这表现形式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精神的存在。”桑树的这种神性,在于它是生命之木。桑树生长数百年的并不少见,甚至可寿达千年;与此同时,它又极易成活,几乎随便剪一个枝条扦插都能活。这种易生之木(如杨柳、竹子,或苗族文化中的枫杨树)都会因这一特质而受人崇拜,张哲俊在《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中指出,《诗经》所谓“南山之桑,北山之杨”不仅仅是比兴,两者也有关系,即它们都生命力极强。俗语所谓“柳树上着刀,桑树上出血”,虽是比喻代人受过,但两者并举,恐怕也因古人注意到,它们都蕴藏着某种生命力。唐人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卷八八木部上“桑”条引《典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虫食叶为文章。人食之,老翁为小童。”这里说的“箕星”乃是风神,而风在古人心目中是宇宙之间流动的气,正如人的呼吸一样,象征着生命。在此竟然认为虫食桑叶可呈现神秘纹样,而人食后可以返老还童。
因此,先秦两汉魏晋的方术书,普遍将桑看作是神树。托名汉东方朔所著《神异经》云:“东方有桑树焉,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其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其上自有蚕,作茧长三尺。缲一茧,得丝一斤。有椹焉,长三尺五寸,围如长。”《太平广记》卷四〇七几乎照抄了这段话,只是在“广六七尺”下加了“名曰桑”三字;而《太平御览》卷九五五则又改成“曰扶桑”。这至少可见北宋时人心目中桑与传说中的神木扶桑是一回事,而这神树上的蚕也具神异,竟一个茧就能有一斤丝。不仅如此,两汉魏晋的文献还传说吃了这种桑树的果实后能成仙,乃是一种不死树(见《海内十洲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很可能发源于以齐鲁为中心的东方。不仅这种神仙思想多在山东半岛滨海地域,而且扶桑这种神木在古典文献记载中也大多出现在东方;而《禹贡》九州中虽有六州(兖、青、徐、荆、豫、扬)提到养蚕和丝织物产,但大多是丝织品,只有兖州提到“桑土既蚕”。胡新生在《中国古代巫术》中认为:“古代神话以桑树为‘东方神木’,所以术士特别看重向东伸展的桑枝和桑根,这一点与迷信东引桃枝别具奇效的观念极为相似。”
与这种原始道教观念对应的是:桑树还被视为生命起源之地,有类西南文化中的葫芦。这也意味着人和树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特别是婴儿从树洞中诞生,体现了对树木生殖能力的崇拜。《吕氏春秋·本味》讲述了商代名臣伊尹身世的神秘传说:“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春秋孔演图》甚至说孔子也生于空桑之中。在这里,“空桑”是一个像葫芦一样的容器,象征着女性的子宫。在神话思想中,中空的树干象征着包含所有生命的容器。在汉语中,“空”的本意就是“孔穴、洞”,联系到老子《道德经》中“空无胜实有”的哲学与道家“神仙洞府”、中国传统婚房称“洞房”,都证明在这种观念中将中空的场所视为孕育生命力量之地。
这种中空之物不仅是生命的诞生地,也是其死后的归宿。古代一些北方民族盛行风葬、树葬,这固然是为了给死者“提供一个临时的居所”,但也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风和树原本是生命的本源,而人死后应回归到这一本源去。桐木中空,在土中易于分解腐烂,但在古代却被视为重要寿材之一,故《吴越春秋》卷五讲到吴王夫差梦见梧桐,公孙圣解梦说:“前园横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为用器,但为盲僮,与死人俱葬也。”桑树也是如此:空桑生人,但据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解释,“桑”也通“丧”,同时代表着出生之口与死亡界的入口。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神话学研究第四卷《裸人》中讨论了拉美神话中的一个现象:“木棉科的树对于从圭亚那直到查科的神话思维所以产生魅力,并不仅仅源于某些客观的、值得注意的特征:树干粗大,木质轻,常有内部空腔。……这种树有着超自然的对应物:其中空树干包含原始水和鱼的世界树,或者天堂之树。”他也注意到伊尹出生于中空桑树的神话,“这种中空的树也许首先是一种容器,用于制造最珍贵的乐器即用一根棒打一个槽那样形式的鼓。中空的桑树和泡桐(即一种桑科植物——就像美洲的无花果——和一种玄参科植物)是基本的树种,分别同东方和北方相联系。”在此他提醒我们注意到天然中空的植物或人工的空腔具备多种功能,这些功能还被原始人认为彼此联系:例如葫芦可以盛水和食物、可烹饪,还是一种可敲打作响的圣乐器。这也解释了中国古代乐器多用桐木和竹子制成的原因,而“空桑”为何又相传是产琴瑟之材的地方,因为音乐、风、生命在先秦的东方文化中是密切关联的元素。
这样,在上古社会从洞穴生活逐渐转向房屋定居的过程中,原本对洞穴的崇拜转向有生命繁殖神力、带有中空的神树。神圣的树林成了人们新的祭坛和庙宇。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指出:“在未有人造庙宇之时,人类有用森林当作庙宇来祀神的,英文庙宇(temple)一字原意便是树木。人类常在森林内寻访神灵,并携带牺牲来供奉它们。”这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例子极多,詹姆斯·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中便谈到各地将树林作为神殿的诸多事例。在云南沧源佤族居住地,每个寨子都有一片神林;路南彝族也会将居住地山上的一块地方划为神林;贵州荔波县瑶山乡的每个瑶族村寨进村小路边的树林里都隐藏着神圣的寨神殿。这些被崇拜的树神,便是人们心目中的村寨保护神,也成为村寨的中心。湘西苗族则喜欢在有高大枫树(苗族的神树)处建寨,并在树下设置祭坛,由此形成公共活动中心。彭一刚在《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中说:“云南大理一带的白族、湘黔一带的苗族,他们分别崇拜不同的树木,村落常选择在有某种树的地方,并在其周围形成公共活动的场地,从而以广场和树作为村寨的标志和中心。”
桑树
上古时代的中原华夏族群其实也大体是同样的生活。中国人对农耕生活惯常重视“农桑”,以“桑麻”为农事代称,而称故乡为“桑梓”,这都不是偶然的。《诗经·小雅·小弁》所谓“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恐怕正是因为这两种树木在当时都是村寨边的神树。虽然目前难以断定中国人何时开始人工栽培桑树,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先秦时代的中原村寨普遍植桑。清朱彬《礼记·祭法训纂》引《五经通义》:“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所谓“社会”,其原始含义就是人们在这些村寨神林之下的公共活动。
黔东南从江县的苗寨岜沙迄今仍保留着这样的景象:村寨里的公共场所是神树环绕的一小块林间空地,这里既是祭祀圣地,也是年轻人谈恋爱的“守垴坡”(意为恋爱之地)。这完全符合先秦中原的生活景象。美国汉学家艾兰在《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一书中说:“在早期文献中‘空桑’是一个很常见的词(有时称作‘穷桑’),它是神灵居住的地方;它也是作为地心(axis mundi)的宇宙之树(cosmic tree)。”当时还有“桑林”这一神圣之地,传说是商国君主汤祈雨的地方,法国汉学家沙畹和葛兰言认为这是土地的祭坛(autel du sol),艾兰则认为应是太阳的祭坛,但更确切地说,这里是祈祷生命繁殖力的圣地。商王在桑林祈雨,恐怕是因为人们观念中这种神树与雷电相关(雷电或许象征着天地的交合),从而能保障作物在土地中的生长——日本人传统上有一种特殊的观念,相信桑林永远不会遭雷击,因此他们在雷雨时反复念叨“桑原”(kuwabara)一词,据信这样就能哄骗雷神而免遭雷击。这可能正是桑林与雷雨联系的信仰残余。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先秦的另一民俗现象:那就是将“桑间”视为谈情说爱之地。因为每个村寨都有神圣的桑林,而此地原本就是祈祷生命繁殖的神殿,男女在此相悦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诗经·鄘风·桑中》所吟咏的,以及所谓“桑间濮上”、“桑间之音”所指的,都是年轻异性在此自由恋爱的情形。准此,《诗经》名篇《氓》所比兴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桑树正象征着两性的情爱。甚至汉乐府诗《陌上桑》也未必只是因“罗敷喜蚕桑”才提到“采桑城南隅”,而有可能是桑树这一象征的遗意。但在汉代之后,随着社会的世俗化,桑树作为神树的意味逐渐被人所遗忘,以致其宗教性内涵对后人而言变得不可索解。
神虫的礼物
之所以要这样说明桑树的神性,我意在重建上古时代中国农业文明的图景:在这样的村寨生活中,“农桑”是密切相关的整体,因而丝绸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新技术发明,而是自然出现的一个生活用品。
毫无疑问,雨水与农业生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雷电不仅带来水,还带来天火。中国古籍一般都记载最初是燧人氏钻木取火,与世界各地相比,中国的火起源神话明显更强调人文因素(见弗雷泽《火起源的神话》),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中国人远古时也相信火是“藏在”木头里,人类只是通过钻木摩擦将之“取出来”。可以想见,夏季的雷雨季会发生雷电击中树木起火的现象,那么对原始人来说,就会认为是神林的桑木内在地“包含”有火种,故据《路史》,桑柘为取火的“五木”之一。这种钻木取火的技能很可能当时是男性所垄断的,由此来看,古代文献所谓“桑弧蓬矢”,很可能并不像《礼记》所说的那样是象征男儿的天地四方之志,而是钻木取火时用的弓钻和引火的蓬草——否则实难想像如何能用弓弦将轻飘飘的蓬草射出多远。此外,由于桑木的这一特性,它就具备了另一重神性,即内含有阳气,因而中医相信桑木条可以“补接阳气,解散郁毒”。
在刀耕火种、以烈火开荒种地的年代,这有着重要意义。故“桑间濮上”的郑卫之地,郑国是在传说中嵩山东麓的“祝融之虚”,而宋国为“大辰之虚”(孟诸泽畔的商丘),陈国为“大皡之虚”(颍水中游的宛丘),它们都被列为“火房”(《左传·昭公十七年》),对应天上的辰星(大火)。值得注意的是,“辰”本意是持锄下地劳作(与“农”的繁体字“農”同源),由此也可见当时观察星象、用火与农业劳动之间存在颇为密切的关系。燧人氏观星的位置就对应于商丘,其活动区域有雷泽——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另一位因善于以烈火开荒的英雄炎帝神农(号“烈山氏”),也定都于商丘(见《寰宇记》:“炎帝神农氏都于商丘”)。而商汤祈雨的桑林也正在这一带——宋都商丘东门为桑林门,东有桑林,遗址即在今商丘市夏邑县桑堌乡。这些恐怕很难说仅仅是巧合,而意味着在上古时代的中原,桑林、雷电、刀耕火种、农业生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鎏金铜蚕
在此情形下,我们不妨设想,对于当时过着这样一种农业生活的社群来说,蚕必定是一种值得特别对待的神虫。他们的生活以农业为主,很难像畜牧民族那样获得大量皮毛,而作为植物纤维的麻和葛只能作为普通衣料,蚕却是以神树桑树的树叶为生的小虫,这意味着它本身也通过吞食桑叶获得了神性。与其它昆虫不同,蚕要眠四次,经历多次蜕皮才能长大,仿佛不断重生。晋张华《博物志》:“蚕三化,先孕而后交,不交者亦产子。”将它看作一种无须有性繁殖的神虫。不仅如此,它还能吐丝成茧,这更是它神性的证明——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宇宙和生命本源往往就是一个卵形的封闭空间,而蚕竟能吐丝后造出这样一个雪白的卵形空间,最终羽毛飞出,简直像是升仙成神一般。没有其它昆虫的茧能像它的看上去这么完美。因此,在俗体楷书中的“蚕”字本义就是天赐的神虫,另一个异体字更明白写作上神下虫。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人们先从蚕本身的蜕变重生中看到其神性,随之认为它所“寄生”的桑树也具有神性。赵丰《桑林与扶桑》一文便主张人们因对蚕蛾的崇敬而产生对桑树的崇拜,进而将桑树看作是天地间沟通的途径,可以在此向天神求子、祈雨。但考虑到不同族群聚落附近都有功能相似的神林,树种却各有不同(如欧洲是橡树,苗族是枫香树),更有可能的恐怕还是蚕因桑林得到关注。不过,这两者之间也有某种相互强化的关系,并因其蕴含的繁殖、生命力、重生、升天等意味而成为这样一个早期文明社崇拜的对象。王永礼在《蚕与龙的渊源》一文中提出,甲骨文中的“龙”字下部很像蚕吐丝,“龙的最初形象,很可能是从蚕的形象演变而来”。他的推论主要是根据字形的相似,以及蚕本身作为可通天神物所受到的崇拜;如果考虑到蚕桑与当时农业生活的密切关联,以及桑林与雷电、火和雨水之间的联系,其论据或可更为坚实,至少可备一说。
王永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昆虫的驯养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远古的中华先民,为什么花费难以想象的精力去驯化这种昆虫呢?”以往有两种点,一是如《中国丝绸史(通论卷)》所引述的“很多人认为丝绸起源的契机在于吃蛹”,是后来才发现丝纤维的利用价值的。这一点也有民族学的佐证:四川大凉山有一支自称“布郎米”的藏族,意为“吃蚕虫的人”,他们最初采集蚕蛹为食,后来才养蚕抽丝。但将蚕蛹作为食物来源既不经济也不合适,并且也不能解释为何在这么多昆虫中唯独选中蚕蛹。另一种观点认为养蚕是为了取丝,但王永礼也否认了这种观点,因为初期“取丝量很有限,为此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也是不可能的”,他由此主张:“远古先民驯化桑蚕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了崇拜与祭祀。”
不过,在接下去的推论中,他和赵丰一样认为,最初驯化喂养蚕的客观原因是为了“保护”它,因为自然环境下它是“一种非常娇弱的动物”。这显然是一种祛魅之后的现代观念,试想一个人怎会觉得神物是“脆弱”的呢?何况现在脆弱的“蚕宝宝”是家蚕,但野蚕可未必——就像家猪看上去不强壮,但远古受人崇拜的野猪可是刚健有力的象征。既然崇拜蚕,那么养蚕本身最初很可能也是一种宗教性仪式。据《礼记·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仭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此处的“公桑”即村寨公共的神林——桑林,并明言另筑蚕室,而这极可能是祭祀蚕神的宗教场所。
蚕茧
在后世的仪式中,蚕室也是祭拜蚕神之地,与此同时,这里又是对男性实施宫刑的残酷刑场——众所周知,司马迁就是被汉武帝下蚕室处以宫刑的。《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唐李贤注:“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据此,这个密室只是照顾到受刑者畏风而特别设置的温暖暗室,这可能表明唐人已不大清楚蚕室的原初含义。在我看来,更合理的解释是:蚕室寓意着人的象征性死亡与重生,就像蚕在破茧后已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与此同时,人们为了避免与接受这样极刑的人接触而沾染污秽,将之隔绝在这样的密室中。日本《古事记》中记载:“修葺无窗户之大殿,产妇进入大殿,用土堵塞入口。”产妇在这个封闭的房子里独自分娩,“这也就是把产房看成和鸟巢一样,产妇在封闭的产房里像鸟生蛋一样安全分娩”。古代普遍将分娩看作是危险而污秽的时刻,因而要让她们在隔绝的密室内生产,蚕室的原理盖在于此,它集神圣与战栗于一体。
不妨设想,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目睹神虫蜕变、羽化飞升,乃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宗教性体验。对于这样的神虫,它所吐的丝自然不是凡物,值得认真对待,因此,丝绸的出现应是在长期过程中自然的发现,而不是为了取丝才养蚕。虽然现代人对蚕多关注幼虫,不像对蝴蝶、蝉等昆虫那样普遍关注其羽化后的成虫,从甲骨文看,“蚕”字字形也像蜷曲的虫子,但篆文蚕字(蠶)已表示“大量虫丝如蓬松卷曲的发髻”之意,许慎《说文解字》:“蠶,任丝也。”由此来看,人们的注意力已放到了它所吐出的丝线上。这种丝线本身也带有神性,《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在此将蚕丝与宇宙间玄妙的音乐之弦丝联系到一起。在晋人王嘉所著《拾遗记》卷十提到的神山员峤山上,蚕丝是一种神物:“有木名猗桑,煎椹以为蜜。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麟,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
对当时人们的生活而言,农桑因而共同构成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食物供应与作为文明基础的衣物,不仅如此,桑林和蚕神还护佑着聚落的繁殖力与生命力。《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载:“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西汉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到当时的大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已可见“男耕女织”在当时便已是社会的普遍分工。到后世,这已演变为对农业文明对蚕神和农事的高度复杂的国家祭祀仪式,北魏太和九年(485)还以国家法定形式规定:十五岁以上成年男子给定露田(只种谷物)四十亩,初受田者每男丁给田二十亩,规定至少种桑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桑田为世业,而每个农户以谷物和丝物作为向国家纳税的物品。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由此可以得到解释:远古中原从事农业生活的人群,将自己的村落视为一块由神树所护佑的圣地,在这样的圣域中,社群的繁衍生息与农业生产的基本保障,均由桑林神树得以保障。与此同时,他们注意到神虫蚕的重生、羽化升天能力,在崇拜祭祀的过程中,他们在有意无意中发现了被自己赋予神性的蚕丝本身的功用,将之织造成了光灿夺目的丝绸。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精选
- 07-10中国超一线明星(一线明星有哪些)
- 06-25星币骑士逆位(塔罗牌星币骑士逆位代表什么意思寓意好不好)
- 07-05星币十正位感情(逆位什么意思)
- 06-28星币9(塔罗牌星币九正位、逆位解析)
- 07-16星币四逆位(塔罗牌星币四逆位是代表什么含义)
- 06-26七杀在迁移宫(七杀星坐守迁移宫代表什么)
- 07-27星币骑士正位(塔罗牌星币骑士正位代表什么意思好不好)
- 06-29星币一正位爱情(塔罗牌星币一正位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 07-01星币9逆位(塔罗牌星币九逆位代表什么意思)
- 07-16星币2逆位(塔罗牌星币二逆位代表什么意思)
星盘查询最新文章



- 10-15林间空地(林间空地英文诗歌)
- 10-15恐怖的纳米机器人(人类的微型科技)
- 10-15梦见别人墙碗(梦见朋友家的碗的预兆)
- 10-15梦见别人在画画(梦见别人画画是什么意思)
- 10-15冼怎么读(冼怎么读 拼音)
- 10-15梦见看望别人(梦见看别人是什么意思)
- 10-15孙德一运势(一个人变富前会有六个征兆孙德一道家智慧)
- 10-15属鸡的虎年什么运势(属鸡人逢虎年的运势)
- 10-15孕妇梦见被别人剪头发(怀孕孕妇梦见被别人剪头发剪短了是什么意思)
- 10-15梦见狗被别人打死了(周公解梦梦到狗被打死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