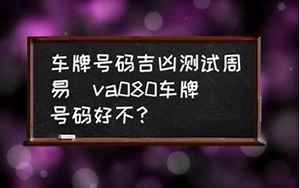鄂君(鄂君启节)
战国《鄂君启金节》——错金铭文精品
战国《鄂君启金节》
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鄂君启金节,也叫鄂君启铜节,战国时期青铜器物,1957年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无讹才发生效力,舟节长30.9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有错金铭文9行165字;车节长9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有错金铭文150字。铭文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是研究战国时楚国交通、政治、经济、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节是水陆交通运输凭证,相当于现在的交通运输通行证。《鄂君启节》于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邱家花园出土,分为舟节和车节两种,是战国中期楚国器,青铜铸造。舟节(右)主要用于水路运输通行;车节(左)主要用于陆路运输通行。使用时货主与官吏各有相同的节,对核后无误才可通行。
此次出土车节3件(形式和铭文均相同),舟节2件(形式和铭文均同)。车节长29.6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弧宽8.0厘米。舟节长31厘米,宽7.2厘米,厚0.7厘米,弧宽8.0厘米。车节为陆路通行政,三件大小相同,可拼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五件可拼成一个完整的)。每件计有铭文9行,行16字,共计150字(重文4字)。舟节为水路通行证,较车节稍长,每件计有铭文9行,行18字,共计165字(重文2字,合文1字)。
金节上的铭文记载了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一个叫鄂君启的人使用的运输货物的免税证件(“鄂君启”中的“鄂”为地名,“启”是鄂君之名。鄂君启,字子皙,是战国时期楚怀王之子)。铭文中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车船大小与数量、运载额、运输货物的种类、禁运货物和纳税及免税情况等。它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
此“金节”用铜铸成,因形似劈开的竹节,故名“节”。这种“车节”和“舟节”,迄今为止仅此一见,因而极为珍贵。为防奸杜伪,在镶嵌工艺的基础上进行“错金银”再创作,故又称《错金鄂君启金节》。错金银也叫“金银错”,其方法是在青铜器铸造时铸出腰槽,将金银片、丝放入槽内,锤打后错实磨平。这一工艺是在春秋时期产生的,应用至今。《鄂君启节》铭文挺拔秀丽,圆润秀劲,庄严肃穆是错金铭文中的精品。
下面4图分别为舟、节上下半部的铭文局部
车节铭文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囗以王命,命集尹囗囗,囗尹逆,囗令阢为鄂君启之囗囗铸金节。车五十乘,岁能返。毋载金、革、黾(渑)、箭,如马、如牛、如特,屯十以当车;车如棓(棒)徒,屯廿廿(二十)棓以当一车,车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昜丘,庚邡城,庚囗禾,庚畐焚(或作埜),庚繁昜,庚高丘,庚下囗(蔡),庚居鄛,庚郢。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
舟节铭文如下: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茂郢之游宫。大工尹囗囗铸金节。屯三舟为舿,五十舿,舿岁能返。自鄂往,逾湖,徒(涉)汉,庚邔,庚芑昜,逾汉,庚郢,逾夏,内囗,逾江,庚囗(彭)囗,庚松昜,内浍江,庚爰陵,徒(涉)江,内湘,庚囗,庚囗昜,内囗,庚鄙,内囗,沅、澧、囗、徒(涉)江,庚木关,庚郢。见其金节毋征,毋舍桴饲;不见其金节则征。如载马、牛、差以出内关,则征于大府,毋征于关。【马骏编辑】
中国历史上第一首译诗,是情歌,可能也是同性恋之歌
作者:老谈
《大宋宫词》开播已久,观众对之爱恨交加,爱它道具纷华靡丽,恨其剧情支离破碎。
电视剧的片头曲,是一首古歌谣《越人歌》,演唱者是谭维维,歌手的唱功自不必说,嗓音沁人心脾,宛转空灵。
但笔者实在不能理解,宋词数量既多,质量又佳,导演何以选择一首远古歌谣,作为描述宋代宫廷生活电视剧的主题曲。
这还不是重点,这首歌谣有很大争议,导演是否真正理解《越人歌》,老谈也是打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纵使《越人歌》写得极美,但以之作为《大宋宫词》片头曲,笔者坚持认为,多少有些望文生义,文不对题。
很多年之前,冯小刚拍过一部《夜宴》,电影中也出现过《越人歌》,周迅与吴彦祖,就是影片的主演。
那时的周迅,比现在更美丽,美如一幅画;那时的吴彦祖,比现在还英气,英气如生风满树。
周迅扮演的青女,着一身素衣,戴一片面具。宫殿的幽香,氤氲了她的素颜;清澈的嗓音,却能穿透一切恍惚与迷漫。
琵琶轻弹,舞袖缓行,歌声悠然:
今夕何夕,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青女的《越人歌》,唱得又缓又慢,在舒缓中犹然透出一股冷峻,那是血溅碧水的声音。
歌声既毕,一场杀伐随即展开。争斗与刺杀,如歌声般舒缓,黑衣黑甲的卫兵,一袭白衣的吴彦祖,就像是在水墨画中杀伐争斗。
周迅所演唱的《越人歌》,显然就是一首情歌。
情歌之谜
从《越人歌》文本来看,它也的确更像一首情歌。
后世的情诗,对其亦有借鉴。譬如,《诗经》当中有一首《绸缪》,诗歌以反复吟诵的方式,戏谑的口吻,比兴的手法,描述新婚闹新房的场景。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中所谓“今夕何夕”,即是对《越人歌》中“今日何日兮”的直接照搬。
《越人歌》的典故,起源于汉代学者刘向,记录的一则故事。
楚王的弟弟名曰鄂君子晳,他乘青翰舟泛游湖泊,趁着鼓声歇停,万籁俱寂之时,爱慕他的越人船夫,对着鄂君身影,唱起这首情歌。
船夫用古越语唱歌,刘向也如实将原文记录下来: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是不是像一篇乱码?看不懂没关系,鄂君当初也听不懂,他让旁人翻译为楚国话,于是便有了传诵千古的《越人歌》之词。
这首情歌,带着淡淡忧伤,旖旎缠绵,鄂君听了也不由动容。
鄂君轻轻走到船夫身边,将她拥入怀抱,又为其盖上锦衣绣被。
很多人以为,唱歌的渔夫,乃是一介女子。譬如唐朝诗人李商隐,作过一首《念远》之诗,其中有如下几句:
皎皎非鸾扇,翘翘失凤簪。
床空鄂君被,杵冷女媭砧。
李商隐写得很有情调,床幔之上,诸物俱备,唯独缺少锦被,所以显得空荡荡。说得就好像,少女在期待王子的到来。
清代大儒梁启超,也认定渔夫即是女子,他还宣布,《越人歌》其实应该是“越女棹歌”。
不论如何,这种解释最是浪漫,自然也更深入人心。
哪怕到了现代,台湾诗人席慕蓉,还将《越人歌》,改编成一首唯美柔和的现代诗歌。
用我清越的歌/用我真挚的诗
用一个自小温顺羞怯的女子
一生中所能
为你准备的极致
在传说里他们喜欢加上美满的结局
只有我才知道/隔着雾湿的芦苇
我是怎样目送着你渐渐远去
席慕蓉直接将“棹船越女”,具象化为“自小、温顺、羞怯的女子”。
在这首现代诗歌的附记里,席慕蓉写出自己对《越人歌》的理解:
有人说,鄂君听懂了这首歌,明白了越女的心迹后,微笑着把她带回去了。但是,在黑暗的河流上,我们所知道的结局不是这样。
席慕蓉的这本诗集,的确就叫《在黑暗的河流上》。笔者读罢附记,却愈发糊涂,真就沉迷在“黑暗的河流上”了。
如席慕蓉所言,我们知道的结局不是这样,那会是怎样呢?原文中可是把结局说得很清楚,鄂君“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颂歌之谜
《越人歌》虽然原唱与译文俱在,但若想读通原歌,困难极大。原因无他,古越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也经历了不断地演变。
首先着手研究《越人歌》之人,并不是浪漫的诗人,而是较真的语言学者。
对《越人歌》进行研读的第一人,乃是韦庆稳先生,韦公是壮族拉丁文字创始人之一。他将乱码一般的原文,解构为壮语,再翻译成汉字:
今夕何夕,舟中何人兮?
大人来自王室,蒙赏识邀请兮,当面致谢意。
欲瞻仰何处访兮,欲待饮何处觅。
仆感恩在心兮,君焉能知之兮?
除韦先生之外,还有别的学者,将原文解构成侗语、占语、甚至马来语,尔后一一翻译解读。
这其实也无可厚非,虽然歌者以“古越语”演唱,但“古越”之地,到底对应今天何地,一直以来,也都是学者争论之所在。
但学者达成的共识是,渔夫应该是一位男士,他以谦卑的姿态,恭维赞美鄂君。
这首《越人歌》,反而是一首颂诗。
渔夫以谄媚迎合的姿态,奉承高贵的君子。鄂君表现得很绅士,原文中所谓“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其实也不是见不得人的羞耻之事。
按照楚人的礼节,鄂君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副绣满花纹的被面,披在他的身上。
学者也论证出,鄂君的举止,没有狎昵的成分,只是一种礼俗罢了。
诚然,早在先秦时代,女生的确和男士一样,善于划船。譬如产生于先秦时代的民歌《河激歌》中,有如下几句:
罚既释兮渎乃清。妾持擑兮操其维。
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櫂兮行勿疑。
一个“妾”字即点明渔夫的性别。
但学者的研究同时表明,为鄂君唱歌的渔夫,应该是个男生。
鄂君所乘坐之舟,可不是一般的筏子,原文上说的是“青翰之舟”,以翠羽和犀尾为饰的华盖,上面还装满乐器,所谓“会钟鼓之声”。
试问,女生有力气驾驭这艘“豪华游轮”吗?
同性恋歌之谜
演唱《越人歌》之渔夫,应该是一个男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越人歌》其实起源于两个故事,两个故事之间,还存在着“套娃”的关系。
话说,楚国襄成君受封之日,他穿翠衣,带玉剑,履缟舄,盛装出行准备渡河。
恰在此时,楚国大夫庄辛经过,庄辛看到襄成君,心里十分欢喜,于是上前行礼,并且很唐突地说道:“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
襄成君忿其僭越的行为,最终不予理睬。庄辛洗了洗手,给襄成君讲起了,前文所述鄂君的故事。
要知道,鄂君官至令尹,这个职位是楚国的最高官衔,执掌一国之国柄,身处上位,以率下民。襄成君不过刚刚册封受爵,人家鄂君显然比他高贵多了。
然而,鄂君犹然可以与渔夫交欢尽意,我堂堂楚国大夫,为何就不能握你襄成君之手?
最后,襄成君果然把手递给了庄辛。
大夫庄辛毫无疑问是男性,他若想反驳襄成君,所例举的渔夫,必然也是男性。
不知诸位发现没有,庄辛与襄成君的故事,渔夫和鄂君的故事,通篇都带有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息。
庄辛先是对襄成君说,“臣愿把君之手。”襄成君最后把手交给他,随口又说了一句话:“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
鄂君就更直接了,听罢渔夫的表白,欣欣然“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越人歌》难道是中国第一首同性恋的赞歌?
学者都研究不通的议题,笔者哪有资格下结论。
好在权威也有了论断。
理学大家朱熹,曾经评价过《越人歌》。他首先对其艺术性,给予了高度评价:“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馀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
但说到《越人歌》之内容,朱圣人以寥寥七字评价:“其义鄙亵不足言。”至于为何鄙亵,朱熹没有明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说呢?
第二个权威,来自于今天的字典。《国语辞典》中,有“鄂君被”词条,它被解释成,“歌咏男女欢爱的典故。”
《国语辞典》其实也说得含糊,恐怕解释成男男欢爱更贴切吧?
权威当然要保持正襟危坐的姿态,而后世的小说家,完全放开了写,就像是挣脱缰绳的野马。
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书中有如下记载:“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你不看别的,只有鄂君绣被的故事。”
另外,将《越人歌》翻译为英文的柏丽尔女士,也倾向于认为,该歌谣乃是“同性恋之歌。”
同性恋行为之对错,笔者不宜发表言论。但将这首充满谜题的古歌谣,用于讴歌北宋真宗皇帝的爱情,着实有些不妥。
但若是导演深谙《越人歌》之奥妙,将对歌曲的诸多谜题,引申为宫廷、宗族、君臣之间的迷离与制约的关系。那导演真是太高了。
对不起导演,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作者-
老谈,always talk,老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7-05深圳五行属什么(请问城市的五行属性)
- 06-29八字 四水(五行八字4个水代表什么五行旺弱怎么算)
- 06-27今年属相(今年的属相是什么属性)
- 06-25四两二钱女命详解(四两二钱女性是什么命)
- 07-03比肩格(比肩格是什么格局)
- 07-11脚踏一星是什么命(脚底痣看今生运势)
- 06-26正官坐正财(正官在时柱的人命运如何)
- 08-25脸代表什么生肖(在算命上脸代表啥生肖的简单介绍)
- 08-05命局土五局(命格土五局是什么命)
- 08-08铃星入子女宫(紫微命盘中子女宫有铃星代表什么)
性格命运最新文章



- 10-04鄂君(鄂君启节)
- 10-04如何供财神(供财神的方法)
- 10-04广东过年习俗(天南海北云过年)
- 10-04梦见和别人一起过桥(梦见与别人一起过桥是什么预兆)
- 10-04adr是什么意思(adr的发展历程)
- 10-04昨日不可留(谜语大全及答案)
- 10-04家和业兴(家和业兴代表什么意思)
- 10-04晚八点是什么时辰(晚上八点是什么时辰)
- 10-04梦见别人家的花开了(梦见别人家花开了好多有什么预兆)
- 10-04属龙(属龙人2023年全年运势及运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