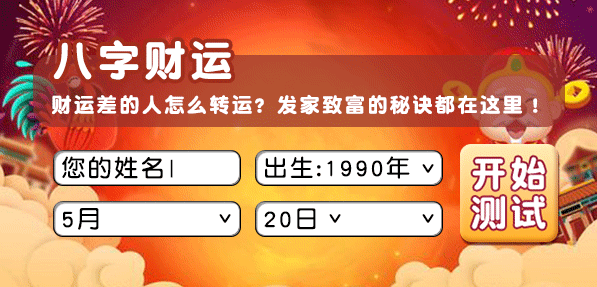梦见掐死虱子发大财(梦见掐死虱子发大财周公解梦)

一部民间《农奴泪》几多血恨示后人
新华社拉萨3月28日电 题:一部民间《农奴泪》 几多血恨示后人——西藏克松村村民自编话剧热演半个世纪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沈虹冰、罗布次仁、薛文献、王泽昊
“西藏改革第一村”——山南市克松村有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话剧:两代村民自编自演,讲述克松庄园农奴赤列多吉一家的悲惨遭遇和翻身得解放的故事。
这部民间话剧叫《农奴泪》。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前夕,记者再访克松村,倾听这部热演了半个世纪的话剧背后的故事。
“观众上台打‘管家’,演员只好躲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山南乃东县郭莎村人头攒动,村民们正在观赏克松村演出队表演的话剧《赤列多吉一家三代六口人的悲惨故事》。
低沉的音乐,衣衫褴褛的农奴,颐指气使的管家……无限现实的场景把人们带到不堪回首的旧西藏——
管家命令赤列多吉看守打麦场,为防偷粮,在粮堆上做了记号。第二天,记号被乌鸦抹掉,管家不分青红皂白,抡起皮鞭抽打赤列多吉。
这时,观众中有人抽泣,有人谩骂,有人扔石头,有人甚至跳上戏台,要揍“管家”。演出被迫中断。
今年70岁的多吉曾饰演赤列多吉的大儿子达瓦,对这一幕记忆犹新:“那时很多群众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受过苦,感触深,看剧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在旧西藏,克松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钦格勒的庄园,农奴被当成“会说话的牛马”,有支不完的差,挨不完的打,吃不上一顿饱饭,受尽欺压。
有一次,赤列多吉饥饿难耐,与狗抢食,被管家毒打。他奋起抗争,结果遭受酷刑,惨死在监狱。妻子嘎多精神失常,消失在茫茫黑夜中。达瓦和弟弟萨波伺机报仇,也被农奴主折磨致死。留下萨波年幼的女儿拉甲艰难度日……
“小时候听母亲讲,真实的赤列多吉死了以后,被抛尸荒野。”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多吉心明眼亮,“他们一家的遭遇,就是广大农奴非人生活的缩影。”
改革后,克松村翻身农奴组成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筹委会,做了自己的主人。1968年,村演出队根据70岁的次仁老人的讲述,编排了这部话剧。
“当时条件很简陋,演员只有14个人,乐器也只有5件。”多吉说,“但大家很投入、很积极,都是义务演出。”
年过花甲的达娃和次仁拉姆饰演女佣和拉甲。谈起当年,两人仿佛重回少女时代,谈到激动处,即兴演唱了一段:
“天上的飞禽中鸟儿最弱小,世间的生灵中农奴最悲惨……”
这部话剧从1968年一直演到1975年。每到农闲,演出队赶着装有道具的马车,徒步深入各县乡村、厂矿、学校演出,累计演出200多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深受欢迎。
“帘子掀开,音乐响起,就让人恐惧和悲伤。”55岁的边巴次仁一直记着小时候观剧的情景。
“我们是真的用鞭子抽,不用力就不像”
2009年3月28日,在西藏自治区设立的第一个“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新版话剧《农奴泪》首次上演,主题依然是“赤列多吉一家的悲惨命运”,但演员几乎都是年轻的新人。演出继续受到热捧,观众为农奴的悲惨境遇痛心疾首,也为管家的残忍凶恶捶胸顿足。
看到剧中管家用皮鞭抽打赤列多吉的孩子时,花甲之年的克松村村民白玛云旦老泪纵横:“农奴主规定,农奴的孩子满8岁就要牧马放羊、支差役,我就是其中之一。”
2008年,拉萨发生严重的烧事件,引发了克松村老人们的深刻反思。为了教育后人,村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牵头,请来曾参演话剧的6位老人,回忆整理剧本,将老版话剧改编为《农奴泪》。
新一代演员没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不知道怎么演。“大家都说农奴苦,但怎么个苦法,我表现不出来。”饰演赤列多吉的白玛扎西说。
白天,他走村串户体验生活,请老人们手把手示范,认真排练,晚上加班背台词。随着对角色的了解,他逐渐走进了赤列多吉的内心。
在剧中,赤列多吉遇到管家,腰弯得差点匍匐在地上。白玛扎西说:“岳父说,农奴见到主人,腰要一直弯着,而且只能看主人的脚面,不能对视,要不然就会挨鞭子。”
白玛扎西的岳父就是多吉。
为把戏演好,他还挨了不少鞭子。
“不用力打就不像。老人们说,管家的语气、眼神就是要凶,下手要狠。”饰演管家的普布多吉说,“我们把牛皮鞭换成了羊毛鞭,藏袍下再垫上纸板,但每次还是把白玛扎西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凝聚两代人心血的《农奴泪》获得了成功。2009年至2011年,这部剧先后在山南、拉萨等地上演,观看人次累计超过3万,许多观众深受感染。
在边巴次仁印象中,每次演出,总有人质疑:“旧社会真的有那么苦吗?”身边的老人就会这样回应:“真的克松庄园比这残忍得多。农奴的血泪只适合在晚上诉说,因为那时遭受的苦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
“参加《农奴泪》的演出,改变了我的人生”
3月的雅砻河谷,杨柳吐绿,田野泛青。
今天的克松村已改称社区,宽阔的水泥路两旁是数十间商铺、茶馆,藏式楼房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门前都停着小车。一些老人坐在门口喝甜茶,晒太阳的年轻人并不多见,都外出务工、求学去了。
正因为人少,《农奴泪》在去年改由乃东区民间艺术团来承接表演。“现在人们都忙,再组织起来演话剧不太现实了。”边巴次仁说,“好在它已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
拥有过《农奴泪》,克松人就有了别样的人生体验。
“过去没想过该怎样生活,别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是这部话剧改变了白玛扎西,“演了《农奴泪》,我知道只要是旧社会,赤列多吉无论如何也躲不过鞭子,再有手艺也没用。现在社会这么好,勤劳就能致富,一定要热爱生活!”
白马扎西后来筹建了一家装修公司,生意好的时候一年收入有70多万元,两个女儿也都考上了大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普布多吉则为这部剧能让更多人受到教育而自豪:“村里有些年轻人游手好闲,看了《农奴泪》,一个个像变了人似的,纷纷出去学手艺去了。”
77岁的索朗顿珠一出生就是克松庄园的农奴,曾和拉甲一起干活,甚至饿得一起吃过虱子。“今天的好生活,过去做梦也想不到。”老人感慨连连。
民改前,克松庄园有59户农奴,302口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今天的克松社区有244户居民,888人,大学生有67人,去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2301元。
不论岁月如何流转,《农奴泪》始终是克松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部话剧让克松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发展生产。”索朗顿珠说,“今天,它继续让克松人明白惠从何来,恩在何处,坚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今后的《农奴泪》寄予厚望:“农奴的衣服是没有色彩的;藏袍里也没有内衣;背着56斤的青稞爬楼梯,步子要稳……一定要用心还原历史!”
“放荡不羁的民谣歌手?您说谁呢?”
采写:董牧孜
原创: 董牧孜 新京报书评周刊 今天
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大学生时,看周云蓬演出,看他觉得有一座山那么壮大,头发像翻滚的海浪,面皮粗糙到不羁的程度,唱阔大又文气的歌,还偷偷在签售时递了仰慕的小纸条。多年以后录节目时再见,发觉人缩了一圈,清瘦,短发,皮肤看起来也不错,像个极稳妥的普通男中年,直至开口讲话才能泄露他有趣的那种。
周云蓬赶紧大呼“放荡不羁的民谣歌手,您说谁呢?民谣歌手都挺老实很养生,熬夜喝大酒的很少了,都那样也活不到今天”,他又补充,“嗨,递纸条有啥用呀,你当年要是递张钱,我还能往包里塞呢”。
01
盲眼人
周云蓬做梦的时候,梦到唱曲儿的同行阿炳。他想写个《阿炳传》,就去了无锡。两个盲眼人见面气氛微妙,胡琴与吉他,讨生活与发财,有过几个女人,什么时候死,聊到最后恶语相向,收割对方,仇深似海。“盲眼人都挺狠的,能活下来,全靠着一股狠劲。”
“你叫周云蓬,号称是你那时候的阿炳。你的歌,还可以凑合着听,不过没太大的根器。你出了点小名,就整日躲在房子里,缺少与人纠缠的因缘,没见过啥世面,也就做做白日梦,所以才梦到我。”
——《遇见阿炳》
著名盲眼音乐人阿炳,是个命运里的狠角色,道士与寡妇的私生子,纵情声色花天酒地过,换来一双盲眼睛。《二泉映月》拉了半辈子,“曲子里装着所有过去未来盲眼人的故事”。
更古早些的著名盲眼音乐人高渐离,也是挺刚。好基友荆轲刺秦失败后,他隐姓埋名,能忍受平庸的日子,但不能忍受平庸的音乐。高渐离的音乐特别好,太好了,始皇帝熏坏他的双眼,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
(最后还是被报复了
),也要听他击筑。
高渐离和阿炳,被今天既搞音乐也搞写作的盲眼人周云蓬写进了小说里,相抗相防又惺惺相惜。
他有个理论,“失明本身是一种血缘关系,可能是灾难造成了这样一种血缘关系。”盲眼人也像某一类种族,跟蒙古族、汉族类似的文化圈,“我跟高渐离、阿炳、荷马,虽然时代不一样,或者国籍不一样,但就是能隔着遥远的时空理解他们”。
周云蓬其实没有阿炳浪,没有老高硬,根据他的描述,在大理定居的生活甚至有点寡淡,大病之后尤其佛系。他的一天,从早上跟导盲犬熊熊散步开始,读书,练琴,偶尔才去古城见个朋友。“在北京扎堆都扎够了,如今要各自为战,搞自己的东西。”
02
讲故事
周云蓬混诗歌圈的时候,以“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闻名的诗人余秀华说,“周哥哥……你的故事比你的诗歌写得好多了。”周云蓬觉得这还是在夸他,“不过就是夸得有点让人觉得心酸。”
人生路上被迫经历了很多,怕浪费了,就有了讲故事的冲动。这也是一个文青的自我修养之路。小时候没什么娱乐生活,就读书上瘾了,跟喝酒上瘾差不多。票友看多了,也想写,于是从资深读者变成了写作者。
民谣圈里比较擅长讲故事的人,除了周云蓬,还有唱《米店》和《白银饭店》的张玮玮,用周云蓬的话说是“比我还能讲故事”,“张玮玮讲故事,慢悠悠有嚼头,像他家乡的拉面,抻起来,甩开去。”他还发现了一个秘密,那些会讲故事的朋友,似乎普通话都有口音。
莫扎特、卡夫卡、伯格曼,可以心向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过自个儿,还是“各安天命,讲讲故事,收敛野心,埋头做个匠人、艺人、说书人。甘于做个二流艺术家挺好的”,周云蓬自己这么写。
“我要求自己在天命之年,老老实实讲点故事。”
讲故事的人已经很少了。那甚至是一种传统手艺,跟吹糖人儿、扎纸船一样,快失传了。
小孩子不再缠着你央求:讲个故事吧。他们更渴望的是,快点拿到你的手机。老人们急着跳广场舞去了,他们再也没故事可讲。搞传销的、传教的、卖心灵鸡汤的,会讲个老鼠尾巴一般短的故事,后面拖拉着一大坨人生哲理。
——《讲故事》
总之,这几年周云蓬歌出得少了,书越出越多。2019年过去四分之三,书就出了两本,旅行散文集《行走的耳朵》和小说文集《笨故事集》。“可能这是时代的病,人们做不同职业,交很多男朋友、女朋友,歌手要写作,写完诗要写小说,从一而终的现代人很少了”。而写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现在一拿起笔,就想写段子。九十年代,爱写终极思考。八十年代,爱山呀海呀地抒情。总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时代喜好什么口味,我就端上什么吃食。我这回不写段子了,写个笨拙的故事,要足够的笨,看得你昏昏欲睡。”
这是《笨故事集》的名字来源。这书里很多篇看着挺像看豆瓣日记,跟周云蓬本人一样松弛,有些跟朋友聊天似的话,又像是在微博里发出来的那种:
“这世界,有人或者狗需要你,有人或者狗想着你,那就是爱,是你跟大地绑在一起的纽带。”
“我只希望上天留下一个姑娘,在远方的某处也向这边走来,但是她要是脾气很坏呢,头发生满虱子呢,最可怕的是她根本不爱我,那就继续向更远处走呗。”
这样的故事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很轻,是随时中断而不会疼的关系,但是感觉留了下来”,是“一个人留在人间的随时断裂的蛛丝马迹”——这是余秀华的诠释,非常现代人的淡薄了,周云蓬觉得余秀华懂他。
03
过日子
盲眼人在古希腊的确有游吟诗人的传统。搞出了永流传的《荷马史诗》的荷马,传说是个盲乐师,兼擅散文与短诗。
可能是失明的灵魂更加自由,盲眼人在讲故事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眼睛看不见,听觉就灵敏,而故事都是在讲和听之间。当我们闭上眼睛,黑暗里涌动的只有声音和感觉,世界在单一的色调上呈现出另外的可能。”说法还是来自余秀华。
周云蓬身上,同时贴着民谣歌手、游吟诗人、作家的标签。不过他最看重的身份还是歌手:“民谣歌手挣钱比较多啊!收入基本全靠演出,出书写诗都只是打打牙祭。”这是个玩笑话,道理却跟古希腊游吟诗人的差不多:巡回演唱是生计所需。
自从有了语音输入之后,搞写作的盲眼人有福了。不用拿笔在纸上戳窟窿,写下来盲文念给别人翻译成汉语。或者像博尔赫斯那样,一个词一个词地吟诵,请别人记录,反复朗诵,推敲修改,如此往复。
周云蓬的《笨故事集》里,能嗅到八卦、情欲和民谣圈轶事,真假参半、欢迎误读的那种——毕竟名人出书,讲的故事往往不能脱离作者的人设。而有大量和性有关的故事,其实是更想发掘身体有障碍的人怎么跟这个世界接触,性的隐秘性怎么体现他们的世界里。
比如《笨故事》,讲盲眼歌手“我”和女大学生建立在崇拜之上的婚姻,如何被小保姆的年轻肉体与丰富所终结。“我们最初对这个世界的温柔都会结束在自己的粗暴里,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和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又是余秀华评)
。生活常常就是没道理。小说是在讲一个故事,而不是在讲一个道理。
再比如《敬亭山》,把唐传奇和清小说吃进去,吐出来盲眼人的现代聊斋。盲眼卖唱歌手与山间茶室女主人,日日喝茶,互道身世,夜里就做起连续剧一样的桃色梦。这个虚构故事的动机,来自有个朋友在半山腰呼唤“周云蓬”的经历。山里有回响,一下子“把你从生活里拉到另一个境界里去了,你就弄不清生活给了你什么启示。”
周云蓬的写作,其实特别忠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从辽宁铁西区来北漂,在北京卖唱时写生活跌打损伤,《黄金粥》这种带着困惑的批判现实;后来一路向南,去绍兴,去大理,南方好像更温暖更阳光,男人更有礼貌,女人性格更温顺,水果更好吃,日子变成在家里坐着读读李白,读读杜甫,还有那种中产文青的旅行,这一切都成了真实生活时,故事也就跟着变了,从北漂伤痕文学到了诗词唐传奇的世界。
不过,“故事本身不是决定性的,讲故事的方式才是。”
短发、瘦削的老周。摄/王大方
小说家不见得要经历过大风大浪和历史转折,还是要善于观察,要热爱自己的生活,还得热爱别人的生活。厌世的人讲不了故事,也没有兴趣观察别人。
——周云蓬@反向流行
海明威写过一个叫《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小说,讲一个小说家临死了,想起来还有好多故事留在心里没写出来。这些故事本来都可以写成好小说的,因为寻欢作乐泡妞喝酒,死神就索命不等人了,从前以为来得及写的故事变得来不及写了。讲述这种遗憾本身,就成了一篇好故事。
无聊的卡夫卡,天天坐在办公室里也成了伟大的小说家。因为这就是他的真实的生活。能不能写一种关于乏味生活的小说——一如我们的生活?比如,关于在家上网的小说,天天做梦的小说,还能伟大吗?周云蓬觉得能行,只是我们很多人没有兴趣和能力把它写成好的小说罢了。
“你只要抓个芝麻,就能把芝麻发展成一个动机,这就是能力。”周云蓬所说的把生活转化成故事的能力,并不容易。那些受过很多苦的人,把这些苦化解成一种自嘲,就能产生幽默——跟逗人发笑的滑稽不一样;而在困境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有钱健康,而是良性的思维能力。想象力也是第一位的,没有想象力,就算让你去趟月球,回来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同样,不见得中国的现实很丰富,就必然产生伟大的作家。
讲故事的人,要热爱自己的生活,还得热爱别人的生活。
本文作者:董牧孜;
编辑:张婷;
校对:薛京宁。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6-28寿香(寿香是什么预兆)
- 06-28刨坟(刨坟是什么意思)
- 07-06馨和歆哪个好(馨哪个寓意更好)
- 06-10胰腺八字五行(胰字五行属什么)
- 06-13胡的八字命理(胡字起名的寓意)
- 06-12肖战算八字(肖战的生辰八字未来运势如何)
- 06-13肉八字(肉字五行属什么)
- 06-13肠胃不好八字(从八字命理谈肠胃不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 06-27梦见鱼头(梦见很多鱼头是什么意思)
- 07-05梦见喂鱼(梦见喂鱼有什么预兆)
双鱼座最新文章



- 10-08梦见掐死虱子发大财(梦见掐死虱子发大财周公解梦)
- 10-08孙思辰(2022世界杯足球解说员孙思辰是后进的吗)
- 10-08属蛇和属兔的合不合(属蛇的和什么属相最配)
- 10-08梦到老虎吃人
- 10-08梦见别人比自己高(梦见别人比自己高很多有什么预兆)
- 10-081691年(1691年属什么生肖)
- 10-08海伦凯勒的作品(海伦凯勒代表作有什么)
- 10-081090年(1090年什么朝代)
- 10-07怎么上香(教你如何拜神灵)
- 10-07梦见分蛋糕给别人吃(老人梦见分蛋糕给别人吃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