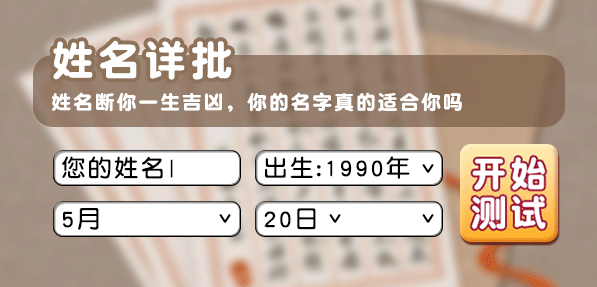日本男名(日本男名 好听的名字)

有些音响设备放日本歌更好听?
最近总是看见一些这样的推荐:坐下来安静的听一听《柳濑小镇》。一听这个名字就像是日本歌曲。而很多人还在想买国产音响系统还是其他国家的音响系统?
到底是想给人一种爱国的精神,还是只是一个幌子。毕竟就算买了国产音响设备,也可能听日本的歌。甚至有些人觉得日本歌放起来更好听?
我觉得日本歌再怎么好听都不去中国的歌好听,那么震撼人心,那么催人泪下,那么具有感化。所以不仅仅要支持国产音响系统,还要好好听一听祖国的歌曲。
国产音响系统选得好不仅省钱,还会让你有不一样的听感体验,怎么不好呢?比如说108、118等,几千块钱就可以搞定一套音响系统,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什么时候看电影就什么时候看电影,何乐而不为之?
名字起得好胜过千万金!男子欣赏一日本作家,只因其名字霸气
读《黑布局》
杯酒在手,高朋满座,诸位既然有这些闲暇,那我就继续讲述一些可能显得有些离奇的事迹,但我保证这些事迹是绝对真实的——那还是我上次回欧洲前好几个月时发生的。
由于罗马、俄罗斯帝国等使节的介绍,尤其是法国使节的大力推荐,我有幸与大苏丹结为相识。大苏丹委托我专程到开罗去,为他办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这件事如此重大,以至于它必须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而除了这个秘密之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另外一件小事,虽然也许同样的使人好奇而无法自拔。
今天下午他们在开会,讲得头大,我也开始头大。基本上头大得不行,下班的时候,我健步如飞,因为有一个头很大的同事就在我后面走,真的是害怕。但其实呢,走得越快越心烦。后来我就去了一家旧书店。那家店的小孩好像有点笨,昨天我给他照相,今天他就跟着我,站在我旁边,还伸手摸我的书包。其实之前我摸过他的头,他的头发好短好短,摸着真舒服。他也很享受似的,就那样扬着头给我摸——怎么说呢,有点像个小动物。很舒服的样子。这样讲也不好,因为人就是人,有尊严有人格,像小动物是不可以的,除非是自己的孩子,而且还不能稍微懂事,一旦学会叫嚣就不好玩了。所以我蛮喜欢那个小孩,摸着他的头,他舒服,我也舒服。但是他们店里没有什么好书,被蚊子咬得不行了,还是没有。
隔壁那家倒有好书,我看来看去还是只要了一本五角丛书,忽然想起来之前答应定浩要给他一本《桃花泉弈谱》——本来有两本,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本也没有了,说不定是已经给他了,但是我却忘记了。只有一本《围棋的宏大构思》,不可以给,不是书好,是那个题目我喜欢。宏大构思,多厉害。书柜里必须摆几本这样的书,再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是必须的,马克思写书都很厉害,起名字厉害。那黑格尔就不行,《小逻辑》,真小。布莱希特却是可以的,《戏剧小工具篇》,这个题目好,谦虚得简直自大。
忽然想起来有个香港写家笔名叫作“加藤鹰”,同行嫉恨道“简直自大得不知廉耻”。我外婆发明很多词语,比如说“写家”,我觉得很好,比“作家”好,作家这个名字不清楚,写家就比较好,而且意思写文章的人还要会写大字。我外婆还发明打火机叫“点火器”,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打火机显得太有科技含量了,其实哪有那么多。
再来说买旧书,武宫正树自然好,藤泽秀行也不坏,但还是武宫好,因为名字有杀气,我也喜欢大竹英雄,这个名字有点像古龙的小说,有欢乐英雄,还有个郭大路。但我不喜欢王动,因为他不爱燕七。燕七有点英伦范,因为大概是个平胸。燕子李三,我也喜欢,因为好像会飞的样子。拼命三郎就不好了,但阿飞正传不错,要是电影才不错,小说还是不行的,因为他太笨。因为他的笨,连带林仙儿也显得不聪明了,因为林仙儿的不够聪明,连带林诗音也不清丽了。但我还喜欢木谷实,因为他的木谷道场好像一个农村合作社的样子,再加上他虽然不笨,但和吴清源一比,就好像榆木脑袋了。既生瑜,何生亮?
但是没办法,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没办法。但是世界上没办法的事情,还是要去做。而且还不能叫苦。叫苦也没用。叫了也没人听。听了也没用。还是一个没办法。但没办法的事情却有没办法的乐趣在。就像吴清源说先着不败是一个千古不易之真理,但他还是要写一本《白布局》,为什么呢?虽然不能打破这个真理,但还是可以写写,因为趣向在这里。下围棋,或者别的游戏,或者生活本身,就是求一个趣向——“趣向”自然是围棋的术语也合适,做生活的概念也合适的。
小时候我下围棋是因为想当孙悟空,要学会天下法术,见一样学一样,没有我不感兴趣的。现在大概也差不多,但知道孙悟空其实也只会七十二变,所以踢足球我还是不会,所以打桌球我还是不会——但也许有天可以去学学,孙悟空取完经过后是不会死的,他是神仙了,大概过后几千年都在学东西。比如说,我觉得爱因斯坦可能是孙悟空变的,也可能最近他变的是博德里亚尔。都是聪明的那种。猪八戒也可以变,他也不死的,但他可能变的是。不晓得还有谁是变来的。也许我也是变来的,但我不知道。我想想看,也许我是二郎神变的,因为他比较好看,只是不要睁第三只眼,那样就不好看了。我也想我是哪吒变来的,这样我的表哥表姐大概就是木吒和金吒,都是笨头笨脑的名字,太好了。
我是下到爸爸让四子过后就再也没进步了。因为就几乎不下了。有一回去同学家玩,和他爸爸下了半局下不下去,没办法下,人家动不动就不应,我是怎么也没办法,我和同学两个人抓耳挠腮也没办法。那一次的表现说明我也可能是孙悟空变的,那同学爸爸就是如来佛。但是他没那么胖,是个瘦人。
再小的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在妈妈单位和一个叔叔下过。那个叔叔会下,我那时候大概算一个普通的劫材都要算到休克的样子。但是中盘的时候,叔叔却表扬了我一手。好像布局布得乱七八糟了,忽然大飞。即使棋力极不相当的时候也可以有妙手,他总需应一手。那么现在想起来,只要能逼到对方不能不应,也就是我的最高境界了。
今天看《白布局》却发现,后着全力追求的也无非就是可以逼到对方不得不应的一手。自然不止一手,因为先着的优势不可能一手就化解,多几次转换,也许可以有一点收获。但却实在是绝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是看《黑布局》却又发现,先着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先着不败是千万年不易之真理,但这棋局却总是一旦开始就要下下去——有一个规则在那里,你若不同意,就不要下棋。既然开始,那就是有胜算,所以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却是这样辛苦。
我后来不下棋,我堂弟却还继续下。我堂弟是个有点木木的孩子,譬如说下棋,我先下,他后下,但他却一直学到中国流,我只晓得秀策流就蛮以为自己成了棋圣传人。再比如我学琴学到外婆说是“好像割鸭脖子老是割不断,害人想提着菜刀来帮忙”,就觉得即使一小也无非如此,我堂弟却正经会吹笛子,现在也还会。这样的事情好多,但我却还是洋洋得意,好像自己比他过得开心。其实也是这样,因为就是比他开心。但是别人比我笨且开心,我就要嘲笑:人笨万事难。
《黑布局》要寄给定浩,他说要我写几个字,我也不知道写什么,所以就不写,但是一边看一边也记点笔记,还把喜欢的谱做了记号,算是雁过留痕——这个词其实很好,有俗气的可以引经据典到泰戈尔的诗,略脱俗的可以提爱默生照抄的印度古话“如果我在飞,我就是翅膀”,但我却老是想成雁过拔毛。然后心里还有相应的对策是一毛不拔。我爸爸说,比铁公鸡更厉害的是糍公鸡,一毛不拔之外还要倒粘走人家的什么。但这个境界我做不到。下棋的时候要做糍公鸡,就是明明执黑还要迫对方大雪崩,实在是坏。又或者着着凌厉,不容对方变化,《白布局》里这样的情形最多,叫人看不下去。想想那时候吴清源二十面打,如果周围都是这样人,脑力消耗是一头,更有一头是实在乏味。乏味啊乏味,真的是乏味。所以这时候明白木谷的好,要是没有他,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不管大小雪崩,他要都是走粘,退,连扳,你可怎么办?
但这回看《黑布局》虽然没什么心得,却也有一点好处,就是我的秀策流偏爱多少有所消退——好古之心大多是虚荣,其实是不懂新知识。以前不喜欢木谷、大竹动辄讲厚味,只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停留于趣向更多,凡事不踏实就没意思,要大砍大杀且拿出凶器来见血封喉,要不总归还是没意思。并不见得比小奸小坏更刺激。我这样的人本来是好什么都不求甚解,现在却真的有些后悔,倘若认真练练手筋,也许多少可以领略一下新布局的厉害,现在却只能看看谱子,并不能够懂得其中的大开大阖大是大非需要一手手地下出来。落子是魄力,但更多是能力。虽然魄力远比能力重要。
但是都不去讲那些无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规则,你参与你就要玩下去,若不好玩自然就开不了头。就像我摸那个智障小孩的头,我喜欢那样摸小动物似地摸他,他也喜欢做小动物来磨蹭我手心。并没有什么或平等什么的,只是很简单的愉快,人就是追求这点愉快罢了。下棋也是这样,所以会得下棋的人知道怎么留出变化的空间,但是怎么留——这个真的是考验人了。因为留出什么样的空间才能大家都有的玩,真是要算无遗策才能实现。且不是一方面算,是双方都要算的。且不是一方算好了,是双方都要算好了的。我不晓得吴清源当年是怎样的感觉,但想来愉快总是有的,并不是一个天才就可以开创新局面,需要的是一群天才。
而在生活里呢,没有这样复杂,或者说远比这复杂,因为生活里你要下模仿棋的话,那简直几乎不可能,没有黑白那样分明的元素,生活是一切游戏创意所基的可怕原料,不能条缕分明有定式可习得,大家都是在心有揣度、惴惴不安、瞻前顾后、贪生怕死……却又这样不晓得疲倦而感觉到有趣。大概就是这样的,在攻与受之间获得均衡。或者就是个算不清的劫材吧,不管到什么岁数,我的水平总之是一算就要算到休克。
2009年6月17日
热门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标签
热门精选
- 06-29癸年是哪些年份(天干为癸的年份)
- 06-18八字带十败(十恶大败日在日柱是什么意思)
- 06-23秋天的6个节气(秋天有几个节气分别是什么)
- 06-10八字带双空亡(八字中的空亡是什么意思)
- 07-06廉贞天府在夫妻宫(廉贞星的含义是什么)
- 06-29武则天真实星座(武则天是什么星座)
- 06-13八字庚金的根(庚金怎么才能富贵)
- 06-14八字庚金喜火(金命为什么喜神为火)
- 07-06今年哪天过年(过年是什么时间)
- 06-16八字带卷舌(八字神煞卷舌星)
天秤座最新文章



- 10-14日本男名(日本男名 好听的名字)
- 10-14梦见别人给别人好多钱(梦见别人给别人钱什么兆头)
- 10-14莨山(中国最美丹霞景区)
- 10-14格局是什么(格局是什么意思含义)
- 10-14家里有蜈蚣(家里有蜈蚣怎么能彻底消灭)
- 10-14梦见买韭菜(梦见买韭菜周公解梦)
- 10-13林肯车价格(林肯买什么车好)
- 10-13四月初五(四月初五是什么星座)
- 10-13最花心的星座男(最渣最花心的星座男)
- 10-13手腕长痣(手腕长痣代表什么意思左手女)